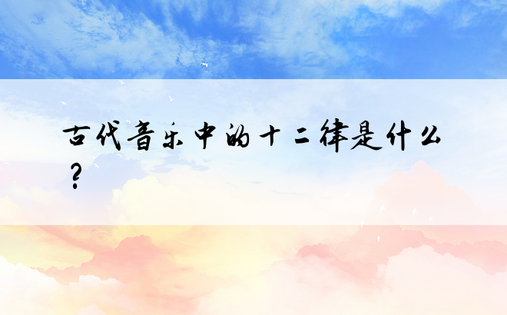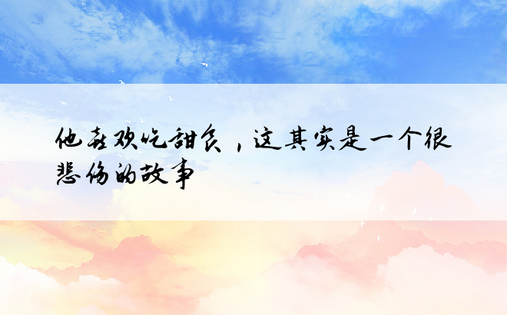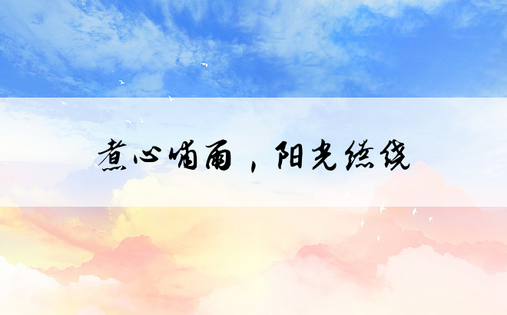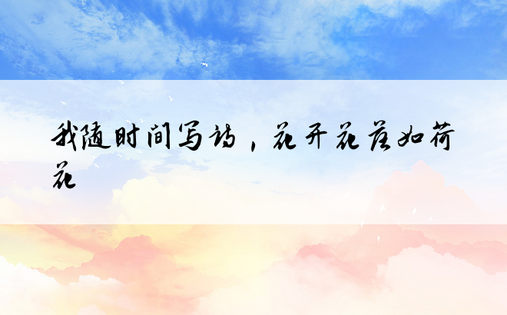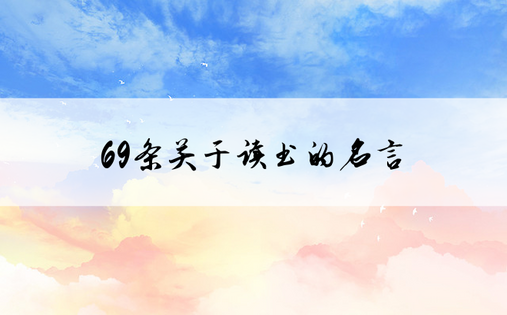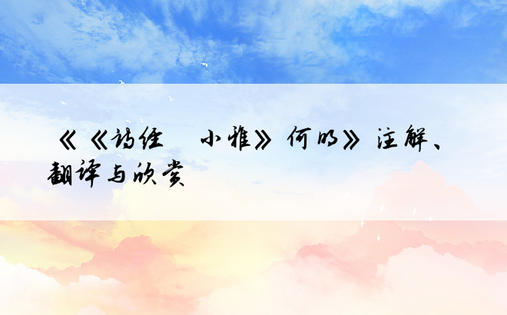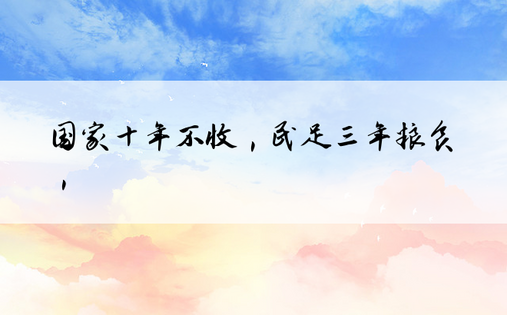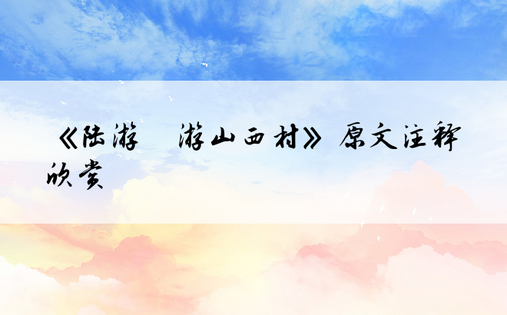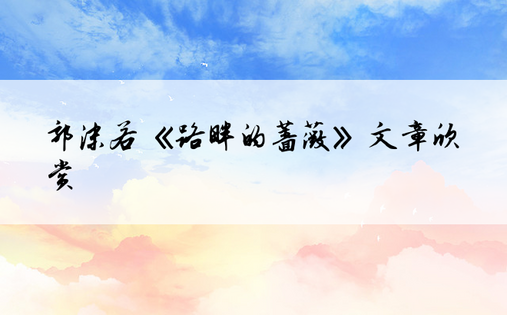汪曾祺《七里茶坊》
2023-10-03 14:08
七里茶馆
我在七里茶馆住了几天。
我很喜欢七里茶馆这个地名。此地距张家口东南七里。那时肯定有一些茶馆。中国的大部分地名都是行路人起的。如三里河、二里沟、三三里铺等。七里茶馆大概也是这样。远道而来的行人来到这里说道:“已经快到了,还有七里路,我们去茶馆喝一杯再走吧。”送客上路,到了这里,客人说道:“已经送他七里外了,请回来吧!”主客到茶馆又喝了一壶茶,说了几句话,出门前互相鞠躬,告别。七里茶馆想必触动了很多人的心。但现在已经没有茶馆了。我四处寻找,却没有人知道这座废墟。 “茶馆”是一句老话,在《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水浒传》中仍然可以看到。现在一般称为“茶馆”。可见此地名历史悠久。
这是中国北方的一个普通小镇。那里是一家供销社,货架上空空如也,只有几包火柴和一堆柿子。两个黑金釉的酒坛擦得光亮,但旁边摆放的酿酒葡萄却是干的。柜台上有一锅用麦麸制成的味噌。有一家理发店,有两把椅子。没有理发师。理发师坐着打瞌睡。一个邮局。一家新华书店只有几套《毛泽东选集》和一些小册子。路口立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鼓励冬天囤积脂肪的快板。文字上署有“文化中心公告”,表明这里有一个文化中心。 Allegretto写道:“天气寒冷冰冻,但我心中拥有整个世界。”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已经过去,这种豪言壮语已经失去了热度。前两天下了一场小雨,雨滴在黑板上划出了一道道划痕。路又宽又脏。两边的房屋也是土墙土顶(这里风雪大,所以房屋大多是平屋顶)。连路边的树木都是黄土的颜色。这座大地色的冬日塞外小镇,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
除了商店之外,这里还有几家大型的车马店。我住在一家大车马店里。
第一次住这么大的车马店。这样的店,一眼就能看出。街门很宽,全天敞开,方便车马进出。进门就是一个很大的空旷庭院。院子里停着几辆大型车辆,车轴向上倾斜,就像几门高射炮。院子的墙边有一个长长的马槽。马槽头上拴着几匹马,面壁吃食,不停地摇尾巴。院子里照例饲养了十多只鸡。由于地上撒满了黑豆、高粱,草丛里撒满了稗子,这些母鸡都长得很肥。有两个房间供人居住,都是大床。我本来想住单间,但是没有。谁会住车马行的单间? “一大碗热腾腾的饭碗”成了这类大店吸引顾客的美誉。
我怎么住到这么大的酒店了?
我在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了两年了。有一天,生产队长来找我,说要派几个人去张家口打扫公厕,让我带他们去。为什么会在我头上?据说以前有两批人去了那里,回来的时候都意见不合。我是一个分散的干部,我在工人中还是有一定的权威的,所以我可以控制他们,等等。到底为什么,我一直不太明白,但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收拾行李了。除了洗漱用品之外,我还带了一根大3B烟斗、一袋掺有半榆叶的烟草、两本四集系列《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上了单人车厢。我们走吧。
我带的三个人是老刘、小王、老乔,包括我在内。
我拿着介绍信去见了市卫生局的一位“负责同志”。他住在污水坑里。一进门,我就闻到了一股奇怪的酸臭味。我交了介绍信,这位同志问我:
“你带来的人怎么样了?”
“怎么样?”
“他们啊啊啊……”
他“啊”了半天,还是找不到合适的词。负责同志大概不太懂读书。我其实明白他的意思。他问的是他们在政治上是否可靠。他担心我带的人会在公厕的污水坑里安放定时炸弹。虽然他也知道这种可能性极小,但他还是问道。但他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也无法说出这份报纸的语言。最后借用一句不太切题的老百姓的话:
“他们的人性是什么样的?”
“人性还是不错的!”
“那就好。”
他松了口气。他把介绍信归档,并为我指定了桥东区的几个公厕。办完事后,他送我出了“办公室”,带我参观了粪场。一侧有几堆干粪,平地上还晾着许多煎饼一样的粪块。
“这都是好东西,没有掺假。”
“粪便还掺假?”
“已添加!”
“要混合什么?土?”
“怎么能和泥土混在一起呢!”
“里面混合了什么?”
“真是个渣男。”
“什么渣男?”
“酱油渣的味道和颜色都和大便一样,而且也是酸的。”
“粪便是酸的吗?”
“发酵。”
于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尝到了纯正的干粪所特有的、无可替代的、持久的酸味。
据老乔告诉我,这位负责同志以前是公私屎,麾下有很多人。他是一个小富翁。后来,他成为卫生局职员,成为一名“公务员”,管理公厕。他目前经营的两个粪场还是很赚钱的。这个男人脸色发紫,嘴巴宽阔,下巴方正,眼睛明亮。虽然没受过什么文化,但是看起来很有能力。虽然他不太会说话,但是在指挥粪工、谈判生意的时候,他所用的语言一定是非常清晰、流畅、有力的。
当你挖公厕的时候,你并不是真的挖它,而是你挖它。天气太冷了,粪坑里的粪便都冻成了固体。您必须使用冰锥将其打碎成一到两英尺见方的不同大小的冰块。可以用铲子把它们挖出来,装上单组卡车,运到七里茶馆,堆在街外的空地上。池底总有一些未冻的稀粪,我就把它刮出来,倒入事先铺好的干土里,调和得像泥一样。将其冷冻过夜。第二天,把它运走。三四天后,当研究所的卡车空了时,又派出一辆三组卡车将积存的粪便和冰块运回研究所。
看看车把式的装载,真有趣。这么重又滑的冰块,依然包装得整齐、严实,即使拉动绊绳,它们也不会动。你可以走一百八十英里而不会丢失它的一部分。这才叫“处理”啊!
“唰——”的一声鞭响,三辆大车离开了。我心里高兴。我们为研究所做了一些事情。我不说我的思想改造得有多好,对粪便的感情有多深,但我知道这东西很贵。我没做什么,只是在地里挖了一点干土和肥料。为了照顾我,不让我去池塘里割冰。至于老乔,大家约定他是来玩的,就是打打闹闹的。这项工作主要是老刘和小王做的。老刘是使用冰箭的高手,小王的实力也很充沛。
这个工作有点脏,但是不累,还挺自由的。
我们住在骆马店的东房,正房是店主一家人住的。南北相对,有一张炕床,每铺可睡七八人——如果挤一点,可睡十人。快过年了,没有其他客人。我们四个人在北边占了一个炕,很宽敞。老乔年纪大了,睡在炕上。小王火力强劲,把门拉到一边。我和老刘睡在一起。我的位置很好,靠近灯,可以看书。两张床之间有一个锅炉。
天一亮,年轻的店主就开门进来,生火,加水,给我们做饭——推油面窝窝。我们带了一袋面条,每餐都吃面条,而且总是点。 ——等我们吃完燕麦片,三组大车又会给我们送来。小王跳下来帮店主拉风箱,我们三个人坐在被子上抱在一起,欣赏他的手艺。 ——这么冷的天,一大早就让他从店主的热床上爬出来给我们做饭,我感到有些遗憾。不一会儿,燕麦面就蒸好了,房间里充满了白色的蒸汽,很温暖,让人慵懒起来。但炕上已经热窝了。刚从抽屉里拿出来的燕麦面太好吃了!我们用蒸麦片面的水洗了脸,然后沾着麦麸做成的大酱吃。没有油,没有醋,特别是没有辣椒!但你要相信我说的是实话:我这辈子很少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那是什么时候? ——1960年!
我们开始工作比较晚。太冷了。而且你必须熬过别人上厕所的高潮。八点多了,我才开着单组车进城。中午就回不来了。有时我会花钱请客,买一包“高价零食”。我会找个背风的角落,蹲下来,我们每人抓几块嚼起来。老乔、我和小王拿了一副老式扑克牌,纸牌和跛七。呼呼的风声中,老刘能把头埋在旧羊皮袄里睡觉,真香啊!下午继续做这件事。我们四点钟装车,五点左右到达七里茶馆。
我们一进门,店主就已经拉动风箱,给炉火加了煤,正在给我们做晚饭。
吃完晚饭,大家各忙各的。老乔看着自己的《啼笑因缘》。他的《啼笑因缘》是一本古书。封面和封底均已丢失。书的角都卷起来了,还有很多缺页。但他仍然戴着老花镜,津津有味地读书,就是读不完。小王写信,或者躺下思考自己的想法。老刘盘腿坐着,一言不发。他可以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很久。在研究所,我看到他去生产队休息一天,他哪儿也不去,什么也不做,只是坐着。我发现不止一个人有这个习惯。辛苦了一整年之后,坐下来休息一天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享受,也是一种迫切的需要。人,有时需要休息。他们不称之为休息,而是称之为“坐一天”。他们请假的理由也是“我想坐一天”。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非常低。我只是靠在床上读杜诗。读完杜的诗,他把它放在枕头下。这是炕,炊烟从炕边的缝隙里逸出,把我的《杜工部诗》的盖子变成了棕色,留下了难忘而美好的回忆。
有时候,我们只是聊天,一句话也不说。吃柿子,喝蒸水,抽掺榆叶的香烟。这支烟是农民装在行李里私自出售的。它的颜色是灰绿色的,不是很浓。吸烟者称之为“半吸”。榆树的叶子着火了,散发出一股烧焦的味道,但又清晰可辨是榆树的味道。这种味道,即使过了很多年,我也无法忘记。
小王和老刘都是“合同工”。他们是根据研究所和公社之间的合同招募的。他们都是柴沟堡人。
老刘是一位老长工,也是一位老光棍。他曾在张家口地区的几个县当过长期劳工。年轻时,他每年都去坝上割燕麦。由于多年担任长工,农耕各方面他都精通。他曾经有一个妻子,因为他无法养活她而离家出走。从此,他不再寻找女人,并且对女人抱有很大的偏见,认为女人是一种负担。他只是背着一包行李——一块毛毡,一床“被子”(即被子),还有一个方头枕头,就到处闲逛。从他行李捆扎的整齐和拎着的样子看,他是一位常年不在家的老长工。他真的很自由,他没有任何衣服,他把所有的钱都喝光了。他不爱说话,但有时他会说话,高兴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这两年,他经常抱怨。原因之一是他不能喝酒。他总是说:“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是怎么发生的?” ——“以前七里茶馆啥都有:驴肉、猪头肉、炖牛蹄、茶叶蛋……通宵卖。酒!现在!怎么了!怎么了!”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梦见娶老婆,是好事!要多久?”年轻时,他曾给八路军送过信,带过路。 “我们队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是给八路军留的!早知道这样,呵呵!……”他说的话常常失控,老乔拦住他:“你胡说什么?约!你没喝酒,你喝醉了!你想‘进去’住几天吗?你没有门可讲,可惜你还活着!”
小王也觉得有些不满。他上高中了。他给自己编了一首顺口溜:“高中毕业,六年的努力都白费了。我想当老师,同学们都叫我哥哥。我想当校友,但我不会算盘!” ”他现在每月收入二十九零六块钱。毛四,如果你想在社会上待一段时间,你吃完饭就所剩无几了。他才二十五岁,并不羡慕老刘自由自在的生活。
老乔,这里大多数人都叫他乔爷。这是一位见多识广、见多识广、见多识广的工人。他怀孕了。年轻时,他在天津学修汽车。抗战时期,他到大后方,在资源委员会运输队当司机,往返仰光、腊戍等地。抗战胜利后,他驾车返回张家口,经常走访坝上各县。后来年纪大了,五十多岁了,血压高了,就不想再跑长途了。他与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有关系。当一台新拖拉机调到研究所时,他就来开拖拉机、修理农机。他的工资很高,而且没有任何负担。农业科学研究所附近的小镇上有一家餐馆,他是常客。餐厅把所有昂贵的新鲜菜肴都保留给他。他有高血压,还喜欢喝酒。餐厅外有一棵大槐树,夏天可以遮荫。休息日,他喝酒,睡在树荫下。树荫在东,所以他就睡在东边;树荫在西边,他就睡在西边,围着大树睡一圈!这是两年前的事了。现在,他很少喝酒了。因为那家餐厅的酒很少会被淋湿。他住在昆明,我也在昆明呆了七八年,所以他总是愿意和我聊天,抽着榆叶烟,一起怀旧。他是一名机械师,所以挖粪不是他的工作,但他自愿报名了。冬天没事干,他就来玩两天。来吧。
这一天,我们很早就下班了。雪下得很大。雪下得这么大啊!
这样的日子,爱喝酒的人都该喝几杯,可是哪里有酒呢?
吃了一会儿面,看了一会儿书,坐了一会儿,想了想,又像往常一样聊天。
和往常一样,总是老乔先开始。因为想喝酒,就讲起了云南酒。城酒、玫瑰崇圣、开远混合果酒、杨林肥酒……
“肥酒?酒和肥肉?”老刘问道。
“酒冒热气时,上面挂着一大块油脂,油脂一滴一滴地滴进酒里,酒是绿色的。”
“喜欢你给我带来的青梅酒吗?”
“看起来不像。那是烧酒,不是甜酒。”
过了一会儿,他说道:“有点像……”
然后我们聊起了昆明的美食。这老乔记性真好。从华山南路、正义路,到金碧路,再到护国路、甬道街,他能数清每一家餐馆。哪家有名菜?详细的。他讲了钱片腿、风干牛肉、鲻鱼锅贴、过桥米线……
“一碗鸡汤,上面有一层油,看上去不热,但是却有一百多度。一盘鸡肉片、里脊片、肉片,都是生的。当你把它们推入鸡汤里,就熟了。”
“那准备好了吗?”
“熟了!”
他又说到汽锅鸡了。它描述了蒸汽锅的样子。锅里没有水,鸡肉是靠蒸汽煮熟的。鸡肉多嫩,汤多鲜……
老刘听得很认真,但他想象不出蒸汽锅是什么样子,也想象不出这道菜的味道。
后来他谈到了昆明的菌类:牛肝菌、青头菇、鸡肉
,连连称赞鸡。
“鸡?这里的蘑菇好吃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品味。”
……
老乔说话的时候,小王好像没在听,躺着看着屋顶。突然他问我:
“老王,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在我去中心化的时候,曾经有人劝我,最好不要告诉农民我的工资有多少。不过,我认识小王一天多了,我不想骗他,所以我就说了实话。小王没有说话,依然睁着眼睛躺着。过了一会儿,他看着屋顶说道:
“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你凭什么赚这么多?”
他没有让我回答,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一阵沉默。
老刘说; “我怪你父亲没有给你提供一本书。老王是大学毕业生了! ”
老乔是个老练的人。他想通了小王这两天为什么发呆,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说道:
“小王,你收到什么信了?拿出来给我看看!”
前天,三辆大卡车来拉粪水时,给小王带来了一封要送到车站的信。
事情是这样的:小王有个约会。这个东西有点奇怪:小王有一个表弟,嫁到了邻村的李家。李家有一个女孩,和小王年纪相仿,也是高中毕业。这位表弟想撮合嫂子和表弟,写了一封信让小王寄照片。照片到了。李家姑娘见状,不服气。恰巧李家的一位同学,陈家的姑娘来拜访。她看着照片,对小王的表弟说:“你知道他们要不要我们吗?”表弟向陈家姑娘要了一张照片并发送给小王。小王很满意。后来,表弟带着陈家的女孩来到了农科院。两人面对面,事情就这么解决了。农村的婚姻往往就是这么简单,不像城里人去公园、走马路、看电影、写情书。
陈家姑娘的照片我们都看过。她很漂亮,有一双大眼睛和两条大辫子。
小王收到的信是表弟写来的,催促他做点什么。他们说女孩们一天天变老,她们等不起了。那意味着春节过后,如果继续推迟的话,恐怕要炸了。
小王担心的是:春节期间他还是什么事都做不成!在柴沟堡地区举办婚礼并不奢侈,但床上有三床新被子,一套花直贡布棉衣,一套灯芯绒长裤和夹克,天鹅绒长裤,皮鞋,运动鞋,尼龙袜子...一般来说是有必要的。陈姑娘没有提出任何额外的要求,她只是想要一支金星笔。这个条件挺好的,小王很喜欢。小王做了长期储备,但算下来,还差五十、六十块钱。
老乔看完信后说:
“就这些吗?值得你这么担心!让老王给你二十,我就给你二十!”
老刘说:“我给你十块钱!现在就给!”说着,他从红布肚兜里掏出一张新的十元钱。
问题解决了,小王高兴又活泼。
于是我们继续聊天。
从云南的鸡到内蒙古的蘑菇。说起蘑菇,老刘可是专家。黑蘑菇、白蘑菇、鸡腿、青腿……
“过了正蓝旗,我就得赶着驴车去采蘑菇。我一天可以提一车!”
不知道为什么又提到都市口。老刘说,他走过的地方没有比独市口更冷的。那是一个风巢。
“我住在独市口,很冷!”老乔说:“那年我们在独市口吃了一洞羊。”
“洞里的羊?”小王很感兴趣。
“风太大了,路边有一个涵洞,快去避风,一眼望去,涵洞是白色的,都是羊,不知道是谁的”是羊啊,估计是被风吹到这里来了,挤在涵洞里,都冻死了。这个好啊,这是一个天然的冷库!我们想吃的话,就进去拖一只进去,整个冬天都吃它!”
老刘说:“肥羊肉炖蘑菇真好吃!四家子的燕麦面比白面还白,坝上真是个好地方。”
话题转向大坝。老乔和老刘轮流说话,我和小王听。
老乔说:坝上地广人稀。只要收获一季的燕麦,就吃不完。以前,山东人出去做手艺,不带钱。聚会结束后,他拿着一大碗米线挨家挨户要面条。 “这里!”说坝上没有果子。怀来人赶着小毛驴车,装了一车山红到坝上。下来后,驴车换成了三辆大马车,车上装满了燕麦面。坝上人民慷慨大方。吃肉的时候,重要的不是重量,而是让你的胃吃饱。他说,坝上人看到坝上人吃一小碗肉,都会惊讶:“吃这个有什么意义?”他说,如果看到江苏、广东人炒菜:几串油菜籽,两三块肉。 ,那就更奇怪了。他还说坝上的女人都很好看。他说,都说水多的地方女人好看,但是大坝上没有水,为什么女人都看上去白皙白皙呢?这么大的风沙里肤色很好。他说他在冲空县见过两个姐妹,长得很像付全香。
老刘和小王都不知道付全祥是谁。
老刘说:坝上土地大,风大,雪大,冰雹也大。他说,有一年固原下了一场大雪,西门外的雪和城墙一样高。同样在固原,有一年下了一场冰雹,其中一个冰雹有马那么大。
“有马那么大吗?掉到你头上也不会死吧?”小王不相信有这么大的冰雹!
老刘还说,坝上人养鸡,但没有鸡舍。白天,打开门,把鸡放出去。鸡到处吃草籽,到处下蛋。他们也不是每天都去捡。过了十天半,我拎着篮子,到处捡鸡蛋,直到装满了。他说,坝上的山都是平平淡淡的,像包子一样。山上没有石头。有些山很奇怪,上面只长着一种东西。有一座山,名叫韭菜山,整座山都长满了韭菜;还有一座牡丹山,夏天的时候山上开满了牡丹花……
老乔和老刘把坝上说得很好,我和小王都觉得这是一个奇妙而美丽的世界。
牡丹山,满山牡丹花开。这是什么场景?
“我们去韭菜山摘两把韭菜,用盐腌一下,明天和面条一起吃。”小王说道。
“妈的!这里会不会有韭菜?山里下大雪了!——把钱收起来!”
虽然聊天很有趣,但也会有兴趣减退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屋顶上的积雪一定有四五英寸厚。我们铺好被子,该睡觉了。
这时,房间的门打开了,店主迎来了三个人。三个人都穿着一件旧羊皮大衣,上面有白色的胡茬,还有及膝的毛毡结。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五十岁左右,长方脸,戴着一顶红狐皮帽。一个四十多岁的矮胖男人,脸上有几道大痘疤,戴着一顶狗皮帽子。另一位是一名与小王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他的眼睛被一顶雪白的羊头帽遮住了,让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女孩。 ——脸色红润,眼睛好漂亮!他们手中都握着一根两尺多长的六纹木短棍。虽然刚才我已经在门外拍了半天,但我的帽子和身上还是粘了很多雪花。
店主说:“给你做饭?-你带面条了吗?”
“随身携带。”
年轻人解开旧羊皮大衣,掏出一个面袋。 ——他把面团袋系在腰带上,难怪看起来鼓鼓囊囊的。
“推哇哇?”
高个子将面袋递给店主:
“不吃麦片面了!吃一天麦片面。你可以到村民家里给我们换点年糕。我好久没吃年糕了,但我想吃一个.把火烧旺,烧点水。我们喝一口。——没有酒吗?”
“不。”
“没有泡菜吗?”
“不。”
“那就吃甜甜的吧!”
老刘小声对我说:“他们是坝上的,坝里的人叫窝窝头巴巴头,他们是牧民、牧牛人,你看他们扛着六纹木棍。”然后,他就勾搭上了这三个坝上人:
“你一大早就离开张北了?”
“是的。——这个天气!”
“就你们三个?”
“还有三个。”
“三个呢?”
“十多里外,有两只牛掉进雪洞里,三人正在努力往上爬。我们先把剩下的牛送到食品公司的屠宰场,在店里等着它们。” ”。
“这种天气还送牛下去吗?”
“没办法了,快过年了,过年的时候我们得请坝下的人吃一口肉!”
不一会儿,店主就送来了一些糕点和一些腌馒头。他们把饼头放进火里烧了一会儿。水开了,他们拍着烧焦的饼头,开始吃喝。
我们的酱碗里还有一点酱,老乔就送给他们了。
“今年那边情况怎么样?”
“好的!”高大男子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显然这是一个讽刺,因为刀疤脸和后生都笑了起来。
“我不是说你去年就跨过了黄河吗?”
“结束了!这还不够!”
老乔知道他话里有话,就问道:
“也是假的?”
“确实如此。我们建立了‘标准场’。”
“什么是‘标准字段’?”
“数一数几块地里收获的粮食。”
“其余的土地?”
“不计算产量。”
“翻坝过黄河?不需要什么‘科学家’就知道行不通!”老刘用了一个很不雅的词,说道:“过‘黄河’,就过河吧!”
老乔向我解释道:“老刘说得对,坝上土层只有五寸,底部全是石头。坝上历来都是粗种少收,主观主义要求单位面积的产出。”
痘疤脸说:“对啊!我们跟公社书记说这个输出是假的,他说:有假就会有真。”
后人云:“也有人说,这就是:以虚实实。”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用想象带来现实”的解释。
高大男子重重叹息:“这年头!官员都撒谎了!”
老刘说:“官员说谎,百姓受苦!”
老乔把烟袋递给他们:
“好牲畜?”
“是的,经不起蹂躏。前两年有大跃进,炼钢,夜战,把牛赶到田里,宰杀,设立一个大田边锅里,大块地煮着。妈的,大家吃吧!你们玩得很开心,现在走吧!-他们三个怎么还没来?快去看看。 ”
高大男子一边说着,一边将解开的旧羊皮大衣紧紧地系紧。
痘疤脸说:“我们两个去,别走。”
“走吧!”
他们和店主从我们车上借了两根木杆和缆绳,打开车门就走了。
听见门外小伙子大喊:“雪下大了!”
老刘起身解手,把三根六巷木棍放在地上,上了炕,说道:
“他们很努力!”
过了一会儿,他自言自语:
“我们也很辛苦。”
老乔上了床说:
“中国人很勤劳!”
小王睡着了。
“过年的时候,我得请坝下的人们吃一口肉!”我心里一直想着大佬的话,感动得久久不能入睡。这是一个简单而美丽的陈述。
半夜,隐约听到有几个人悄悄走进来。我睁开眼睛问道:
“牛来了?”
高大男子轻声道:
“我知道了。我把你吵醒了!去睡觉吧!”
他们睡在对面的炕上。
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晚。等我醒来时,那六个赶牛的坝上人已经不见了。
写于1981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