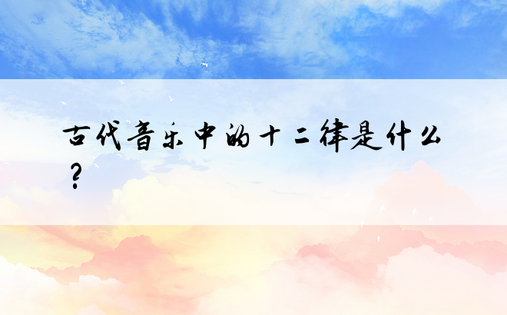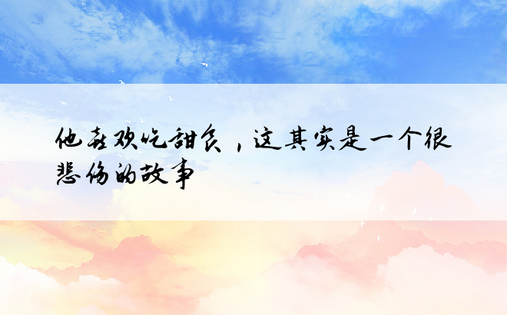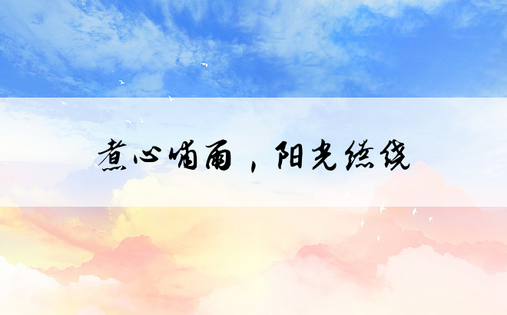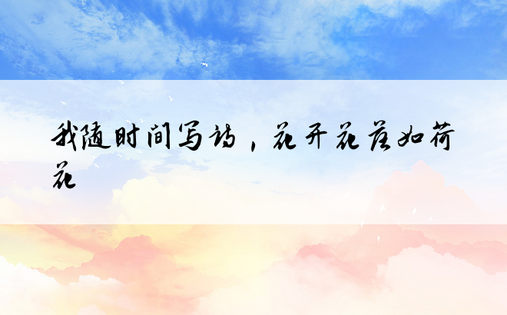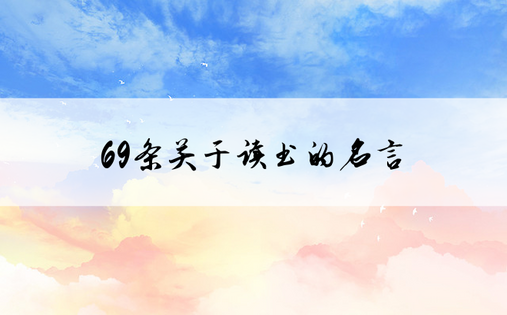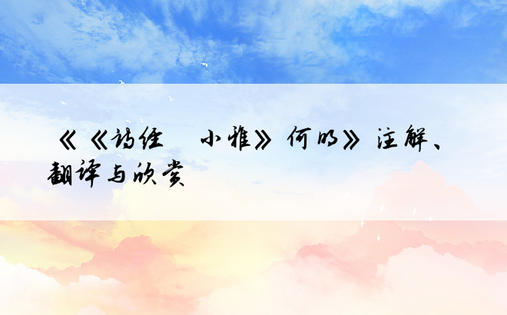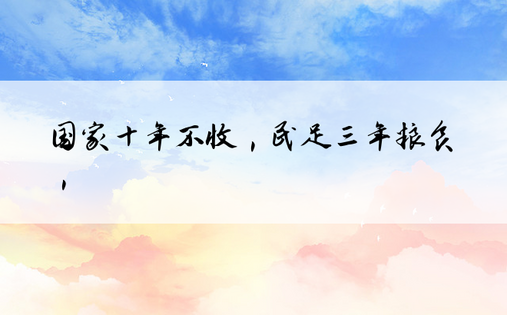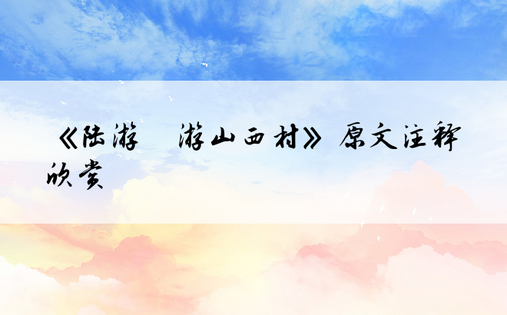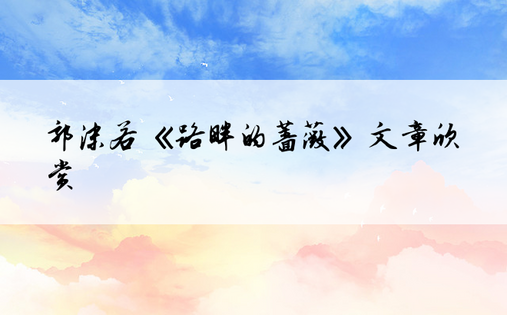舒国英:《法学理论》:概念与意义
2023-10-02 01:34
法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完全遵循自然科学的范式和方法规律,也不能说其学科的形成是自然控制下的“知识群体”的结果。科学。我们看到,自然科学的普遍性及其衍生出效果明显的技术的独特优势,并没有完全取代知识领域法律人的思维和法学家的工作方法。特别是,自然科学无法取代法学家建构法律知识的方式和法学家解释法律的方式。由于这一立场,现任范德比尔特大学(简称“范德比尔特大学”)法学和政治学教授的爱德华·L·鲁宾(Edward L. Rubin)成为《法哲学与法理论指南》(A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gal Theory,1996)中指出的“法律学术”条目:“法律学者将法律视为一组由人们设计为意义系统的规范性陈述。陈述)来研究……他们考察法律的内部结构和意义。”在笔者看来,鲁宾所谓的“法律的内部结构和意义”实际上是“法理学”。
但什么是“法理学”? “法理学”能否认识并描述它?如何认识和描述?要想明确法律知识的本质,首先需要研究上述问题
01 中西文学中“原则”与“法理”的表述
有必要从词源上梳理一下“法学”一词的含义。我们先来看看汉语中“礼”的用法:毫无疑问,“礼”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具有丰富语义的汉字。其所指对象和含义差异很大。它可以指“物质组织的条纹”(纹理)或“理”。指“事物的内在理”(事理),也可指“所”(管理、处理事物),与“法”、“物”、“情”、“义”有关, “天”、“人”等组合组合成不同的汉语词语:如汉代班固《汉书·宣帝纪》载:“孝玄之治,信信必罚,全面验证名实、政事、文学、法学者,皆精于能。”这是在讲“法理”时,实际上就是“立法”(法律的管理者)。翻译成现代汉语,“法学家”指“司法人员”或“司法机关”(故郑玄注:“礼,亦狱官”)。魏末晋初法学家张飞在《律注表》/《律注要略》中也表达了“礼”的思想:“夫礼,是玄奥玄奥,不能以一种方式修行;法是秘密中的秘密,你不能把它放在一起。” “治夫者,当慎其变,究其原因”。 “刑夫者,为政之官;有理者,为申情之机;有情者,为心灵使者。”例如:“惩罚丈夫的人是心灵的代理人。”杀手是冬日颤抖的太阳的形象,罪人是秋天钳子落下的变化,救赎者是春阳悔恨和吝啬的过错。”
《唐律疏议》含有许多与“理”相关的规定:例如《名例》的《十恶》文中简述:“五从近亲,互相残杀,穷尽万恶,叛逆,违背人理” ,故名恶逆。” 《贼盗》《夜间无故进入别人家》一文中说:“夜间进入别人家的原因可能很难判断,即使你知道罪名,你仍然是罪人。”该罪是基于赎罪理论。是非原则平等。”《户婚》《答》《有妻则可多娶》一文曰:“一夫一女,无婚姻。有老婆了,再娶多了,就成不了老婆了。请详细询问理由。有学者认为,《唐律》中的“理”是价值判断的基础,是唐代判断犯罪的“第三法源”。君臣、父子关系)、“言理”(涉及言语内容)、“词理”、“情”(情节、事实,包括行为动机和目的)等;其次、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处理事物的方式,即“理”,而法律都是判断是非、判断是否犯罪的依据,其本质在于“义” (义包括礼);三、“天志”、“天长”(天的共理、正道、德性,自然的运行法则,用来规范人事)和“天理” (代表天地阴阳四时自然法则,宋代以后也沿用)表达“三纲五恒”的人类伦理原则)。一般来说,中国古代所谓的“理”可以解释为“判断是非的依据”,或者“正当理由”、“原则”和“行为的正当性”。 “理”也可以用作推论词,如“理”、“义”、“无理”、“不合理”、“不合理”、“合理”、“不合理”等。在《唐代律令》中的“理”中,他指出:“服从天和人的原则,可以视为广义的原则;论人性的原则,可以视为狭义的原则。”意义;而法律法规正是规定人性的规则。”道理,所以法律和命令所包含的原则可以称为狭义的原则,即原则。”沈家本在总结中国古代刑法的原则时,沈家本也说:“事情发生的越多,就越密集。法律的原则,但总的来说无非就是‘理性’。”
在西方语言中,“Li”也用作名词和动词。作为名词,“原因”通常有四种含义:(1)解释某事导致某种状态(或:某事为何发生)的“原因”; (2)解释或证明某人做出、思考或说出某事的“理由”或“理由”(推理基础); (3) 使做某事或感觉某事合法且适当的事实、条件、情况或动机(“合理”); (4)逻辑性的理解和思考,理解、判断(辨别是非、是非)、确信、计算、衡量和判断的(健康的)心理能力或心态(“理性”、“理性”)决定。 “推理”作为动词,主要指“推理”,即运用逻辑方法进行思考,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或判断。在英语中,“reason”一词可以表达为reason(源自法语raison,古法语写成:reisun)。这个词最早起源于希腊语“Logos”(λ?γο?,logos),在罗马时代,它被翻译成拉丁语ratio,意思是“金钱的计算”。在英语中,“法律原则”一词可译为法律的原因,与拉丁语的ratio juris相对应。与这个词相关的是“ratiolegis”,它强调“理由”来自于法规的字面,前者强调“理由”不包含在法规体系本身中。它们可以被称为“更高的规则”或“一般原则”),现行的法律规则只是这一“法律原则”逻辑推演的后果(结果)。在拉丁语格言中,我们可以找到更多关于“理性”或“法律原则”的表达:如,“Eadem estratio,eademestlex”(Eademestratio,eademestlex)、“Eademestratio,eademestlex” (Ratio non clauditur loco)、“法律是法律的灵魂”(Ratio Legis est anima Legis)、“法律是公正的平衡”(Ratio in jure aequitas integra)、“法律是法律的源泉和理由”习惯”(Ratio est formalis causa consuetudinis)、“Ratio est Legis anima; mutata Legis Ratione mutatur et lex”(Ratio est Legis anima; mutata Legis Ratione mutatur et lex)、“理性是法律的灵魂。当法律原则改变,法律也会改变”Quaere de d“法律是理性的命令”、“法律总是以理性为目标”、“法律与理性是一致的”、“Lex plus laudatur quando Ratione probatur”、“理性与权威是世界上最明亮的两盏灯”、“自然在所有人之间建立的规则称为自然秩序在所有人之间建立的称为万国法),等等。
02“理”与“道”的哲学解释
无论如何,在中国古代和西方的法律文献中,“理”、“法理”等词语的使用并不统一,是受上下文制约的。要想对问题有更清晰的把握,就必须对此类概念的词源和意义变化有更统一、明确的认定。
我们先来考察一个哲学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原则”和“法律原则”是“独立于思想的现实”吗?如果它们是“独立于心的现实”,那么它们是什么样的现实呢?显然,这里必须从本体论的角度讨论“原则”和“法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还是在西方文学中,“理”和“道”两个词总是紧密相连的。
例如,古希腊语“逻各斯”(拉丁译:比率)常被说成是宇宙秩序和人类知识的“原始原理”(赫拉克利特)或“渗透宇宙并使其不朽的力量”。 ”实证原理”、“宇宙的生成原理”(斯多葛主义)。当然,“logos”这个词还有很多其他的用法,比如“理由”、“请求”、“意见”、“期望”、“词”(词)、“言论”、“帐户”、“比例”、词源变化历史悠久(包括希腊化时期的罗马拉丁语翻译,《新约》,以及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解释[例如,《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在开始时”)是道,道与神同在”,将“基督”与“道”/逻各斯等同起来,说耶稣“道成肉身”]等等)需要特殊的词源考古学。
无论如何,“逻各斯”作为哲学术语的指称并不是特别固定的。因此,对于这个词的使用,笔者关心三个问题:(1)“逻各斯”指宇宙(世界)生成的最初“基础”(原理/原理)或统一的内部秩序结构。宇宙(世界)的(“理则”在这个意义上最好理解为宇宙[世界]的“道”)? (2)还是指我们人类通过“冥想”来反映(再现)宇宙(世界)的“道”的“理”(在这个意义上,“理”就是宇宙(世界)的“道”)宇宙(世界)镜像)?或者,(3)“理”既包含宇宙的“道”又包含“理”?笔者认为,西方古代圣贤对上述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同样的情况也反映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例如春秋末期道教创始人老子(老聃,名李耳,生卒不详)在《道德经》中说道: “有物混杂,先于天地而生。。寂而荒凉,独立而不变,行而无危,可为天地之母。不知其名,但字是道,强名是达。” “道冲而用,未必满。深渊如万物之祖,挫其锐,解其惑,和其光,同其尘。深如或存在,不知谁的儿子是第一个相帝。”按照他的说法,“道”是万物存在的本原(“万物的本源”),其之上再无任何本原的存在(“先生于天地”,“能为天地之母”)。 ”,“前面是象皇帝”)。战国中期道家代表人物庄周(约公元前369年-约公元前286/275年)在《庄子·缮性》中说:“道是理……道,皆有理义。” ”。他较早将“道”与“道”进行比较。 “原理”相互解释。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在解释老子《道德经》(《解老》)关于“道”、“礼”时也指出:“道理,是理的基础。理,是使事物发生的文字;道,是万物被造的理由。所以说:“道,是事物被造的原因。”物有理而不能比,物有理而不能比,所以理是事物的主宰,万物有不同的理,万物有不同的理而道则穷尽……道的情感是无法控制的、无形的、微弱的、随时对应的道理。”他认识到“道”是“一切理的集合”(一切理的基础)或者说“道”与“理”是同一的。也有人说“道”是一切事物产生的原因。物(万物形成的原因),其含义并不统一。曹魏学者王弼(226-249)在其著作《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解释道:“物有本源,物有主” 。虽然路径不同,但(同)目的地是相同的。虽有百种考量,却是一致的。”道有大理大义……道不能见之可见,听之不闻,斗得之……。是知事物的本源,所以虽然看不见,但是是非之理却可以知道,可以命名。”
到了宋明时期,中国对“道”、“礼”的解释有了新的发展,其中还涉及到对“德”、“礼”、“心”等概念的分析,其影响力超过了“儒家”。汉代经典”。 、南北朝魏晋时期的“玄学”和隋唐时期的“佛学”:例如北宋周敦颐(1017-1073)用《易》的“阴”和阳”与“太极”解释“道”、“理”、“理”、“诚”,提出“太极无极”的理论,即“天道”的本体论思想。一实即一切”、“诚为本”:“诚是圣人之本。”“诚是五恒之本,百行之本也。” ” “礼就是原则;音乐意味着和谐。 ……阴阳调和而后调和。主、臣、父、子、兄、弟、弟、夫、妻,万物各有规律,然后和谐。故礼为先,乐为后。”张载(1020-1077)在区分“闻见之知”(闻见之知)与“德之知”(天德良心)的基础上),提出:“先德良知”,天下之理曰道,天下之理曰德。 (清王辅之解释道:“道理,事物都是一样的,事物本来的样子,是世人所知道的,遵循它们就可以得到。不象这个外道棍子。” ”)南宋朱熹(1130-1200)继承二程(程浩、程颐)之学,写下《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的著作提出了系统的理学(又称道、性理、理)思想,如《理一分术》(“万物皆有此理,万物皆有此理”)。原则来自同一个原则”)。 。但它们所占据的位置不同,其原理的用途也不同。”“一草一木都有它的原理。”“每一个原理都极其极端,穷尽到底”),“先知后行”到了明朝中叶,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9)主张“良知”(一种超验的道德意识):“良知是道法的本质。学说认为天理在人心(“心之体是性,性是理”, “心外无一物,心外无一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慈”),并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知识就是行动”、“行动就是知识”、“知识就是行动”、“知识决定行动”)正所谓“知识是行动的思想,行动是认识的努力”“知识是开始”行动,行动是知识的完成。”
一般来说,如何理解“理”及其与“道”的关系,取决于思想家持何种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如果坚持王阳明的心观,所谓“心外无物,心外无物”。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那么,就本体论而言,“理”、“道”、“心”其实并无区别,而就认识论而言,“知”张载提出“遵循天地之理曰道,得天地之理曰德”,似乎是对“理”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关系的简要说明。 ”,“道”和“道德”,但我们如何“知道”这并不是一眼就能理解的。古希腊对“逻各斯”一词的理解也很相似。它的最初含义和派生含义相互交织,对这个词本身的分析,就构成了一门高深的学问。然而,如果我们放弃许多派生用法,那么就哲学本体论而言,“Logos”究竟应该译为“道”还是“理”,从意义上讲,恐怕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争议也必定存在。不可避免的。
笔者认为,面对自古以来诸多圣人思考过(甚至提出过系统理论解释)的概念,我们首先应该“悬置”各自对“理”的实质性理论认识,从事物(问题)入手。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样的理解方式才是可取的,或者说它对于解决“理性”概念的解释问题可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历代思想家首先是在本体论层面对“理性”概念进行了阐释:如前所述,古希腊哲学家和中世纪神学家普遍采用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即承认“道”。 ”/“理”(“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根本)基础(因),是人类社会固有的客观本质。老子(老聃)的道家思想,韩非的认识旧说,而宋明理学所讲授的“理”/“道”,基本上采取了同样的理解和理解方式。换句话说,早期人类思想家似乎认为“道”/“理”是一种外在世界的客观存在,即“独立于心的实在”,它构成了人类认知的对象。但作为“道”/“理”的“外在世界的客观存在”又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分析起来,这句话本身的含义也很模糊)?但对于这一点,思想家们似乎有不同的认知维度和角度。我们尝试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希腊语:α?τιον)来观察他们的观点。理解上的差异:有的从“物因”的角度来解释“道”/“理”(例如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万物的本源是原子和虚空。原子不可再分物质粒子,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地方],中国古代“五行”理论[金、木、水、火、土]);有的从“动力因”的角度来解释“道”/“理”(如古希腊恩培多克勒的“爱恨”理论【“爱”指促进四根合一的力量)并创造万物;“嗔”是指促进四根分离、造就万物分离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并存于世间,正在经历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它们,和“Nus”一样,也是存在于事物之外的动力】,赫拉克利特的“火”理论【宇宙对于万物来说都是一样的,它既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人类创造的。它曾经是、现在是、也是如此永远是不灭的活火,按一定程度燃烧,按一定程度熄灭],中国的“阴阳”理论);有的从“形式因”来解释“道”/“理”(例如毕达哥拉斯的“数”论【数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数量上的矛盾关系可以推导出有限与无限,一与多、奇数与偶数、正方形与长方形、善与恶、光与暗、直与曲、左与右、阳与阴、动与静等等]以及柏拉图的“观念”理论[观念是永恒不变,它们是普遍的、绝对的、必然的存在。可知的观念是感性事物的基础和原因,感性的事物是可知性观念的派生物。”理论),有的解释“道”/“理” 》从“终极因”出发(例如古希腊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和阿那克萨戈拉的“理性”论【以永恒不变的变化的“存在”为万物之本,强调因果的同一性,并用“理”作为安排万物秩序的“善”,显示其倾向],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等)。
无论从“四因”中的哪一个“因”来看,自然哲学本体论中的“道”/“理”都是与外部世界的事物(实体)相关的客观实在,但这个客观实在实在不能等同于客观事物(实体)本身,而是客观事物产生、变化、完善(优化)和消亡的必然表现方式(道),或者嵌入在这种必然方式所形成的条件结构中。推介会。基础(康德称之为“因果决定基础”[die Bestimmungsgründe der Kausalität])。这种必然的呈现方式(自然之道,或:自然事物的必然呈现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条件结构所蕴含的基础(自然原理,或:决定自然事物发生原因的基础)它们根据我们对它们的理解自由存在,即独立于我们的思想,因此是客观的(“自然原理”也可以定义为“自然事物的客观和因果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五点:第一,在自然哲学的本体论中,既有自然事物的客观“道”(自然之道),也有自然事物的客观“理”(自然之理)。 。 )。前者是事物(自然/外部世界)的产生、变化、完善(优化)和消亡的必然呈现方式(自然法,“必然王国”的法则),后者则嵌入在自然必然的表现方式所形成的条件结构。依据(必然的因果基础):例如,如果“适者生存”是生物进化的必然方式(“道”),那么生物体在特定环境下的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就会导致适应。穷人的生存和不适者(劣等者)的淘汰(灭绝)的因果基础是必然的呈现方式所形成的“理”。其次,很明显,“道”和“理”是自然哲学本体论中略有不同的术语。它们有不同的含义,不能完全混淆。说“道”与“理”相同,可能只是有一定的含义。修辞(隐喻)的意义。当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理”与“道”密不可分,“理”是“道”的原则,所以统称为“理”。但也不能反过来说,“道”就是“理”之道,有所谓“理之道”。这完全颠倒了知识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利于我们对“道”的理解。第三,正确的方法是由“理”而知“道”,而不是相反,先讲“道”而后知“理”。有时,我们掌握了某种自然/外部世界(即所谓(得“道”)的必然呈现方式,但不一定完全清楚这种必然呈现方式所形成的条件结构所蕴含的基础) (因果基础),也就是说,不一定知道“道”的“理”。第四,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四因”既不是具体的“道”,也不是具体的“因”,而是抽象的。理解具体“道”/“理”的维度或角度。一切自然事物的“道”/“理”都可以从“四因”的角度来观察或理解。第五,说万物为一或者说,只有在以下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即任何(自然/外部世界)事物都有必然的生成、变化、完善(优化)、消亡或其形成的方式。嵌入各种条件结构的基础(因果关系的决定依据),而从抽象的角度来看,一切自然必然的表现方式(规律/规律)都具有相同(相同)的特征,如“必然性”(必然性)、“规律性”、“有序性”但并不能由此推断出万物自然的、必然的表现方式或者其形成的内在根据(因果决定根据)都是相同的或相同的。相反,不同的具体事物出现的必然方式或嵌入其形成的条件结构中的基础(因果决定的根源)根据)不同,我们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不同具体事物的生成、变化、完善(优化)、消亡的“四因”结构其实是不同的:例如生物和无机物生成的必然呈现方式、变化、完善(优化)和消亡以及所形成的条件结构的嵌入基础(因果规定基础)不能一律归结为“适者生存”。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生物进化 必然的呈现方式(生物进化规律/进化方式)部分相似,但生存(生命)的必然呈现方式(生存法则/生命,或:生存/生活方式) )有本质上的不同(人们用他们所做的事情来制定法律来规范他们的生活,其他动物则受到直接的丛林法则的约束)。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自然哲学的本体论“道”/“理”是可以被认识或发现的,进而可以被表达的。所说的“理”可以称为“言语理”,它以人类言语陈述(命题)的形式存在。从本质上讲,“理”应该是自然哲学本体论中“道”/“理”的正确表达,即所说的“理”与自然的生成、变化、完善(优化)和灭亡有关。的客观事物。如果以此方式形成的条件结构所蕴含的必然呈现方式(道)或依据(理)是一致的,那么认识论意义上的“理”和本体论意义上的“理”就应该是同构的(Isotype),或者说“理性”应该是客观“理性”的反思(反思)和复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的“理”也可以称为“理”(对客观“道”/“理”的正确解释)。就自然哲学中“道”/“理”的本体论而言,具体而言,由于它们的陈述涉及对“道”/“理”真实性的承诺,因此可以称为狭义的“真理”(对于这个概念的分析,见下文)。但另一方面,日常言语本身可能反映也可能不反映自然哲学的本体论“道”/“理”,甚至可能是对后者的误解或故意曲解。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理”中的“理”可能是认识论中纯粹论证中使用的概念——“理性”(推理基础)或“理性”(通常指事物的“正当化”(推理基础))。论证和评价)。描述支持说话者主张的事实和数据时的逻辑诉求),它们也可能被说话者滥用,成为“错误推理”、“反常推理”和“借口”的代名词。显然,“错误理由”、“错误理由”意义上的所谓“理由”是用词不正确,不能称之为“理由”。
03 “法理”的本体论与认识论
了解了这些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研究一下“法理”问题。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法理”显然没有嵌入本体论中客观事物的生成、变化、完善(优化)和消亡的自然必然的表现方式(自然之道)所形成的条件结构中。自然哲学。基于(自然原理,即自然因果关系意义上规定的原因基础),因为“规律”在物理意义上不属于客观事物(实体)本身。另一方面,“法律原则”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法律存在的原则”。这里的“法律存在的理由”可以理解为法律整体存在的理由(法律存在的因果基础),或者说是产生、变化、完善(优化)的“道”。以及法律本身的消亡。嵌入各种条件结构的基础(内部因果规定基础)。例如,法律为什么会产生、变化和消亡?佛法能永远存在吗?法律为什么具有有效性和效力?诸如此类的问题属于“法律存在原则”问题(可以构成法律史、法律社会学等讨论的主题),而不是我们这里具体讨论的“法律原则”问题。研究“法律存在的理由”固然重要,但这种研究可能属于“关于法律”的研究,而不属于原本的法学(法学说)。
为了解释上述观点,我们必须明确,所谓“法理”实际上是指法律法规或法律规范所规定的处理事项的结构和法律后果,特别是行为要件(或“事实类型”)。 ”条件)办理事宜。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嵌入要素结构的基础(合理规制基础)称为“法律规范/法律规制的基础”。例如,刑法规定人民有正当防卫的权利。自己或者他人遭受不法侵害时,出于自卫的需要,为保护自己或者他人而采取防卫措施的,不负刑事责任。这种规定本身(我们不妨称之为“规范道”)并不是客观事物必然呈现(自然道)的表达,而是一种以“祈使句”(命令句)形式表现出来的“正当防卫”规范。辩护方式),该规范之所以具有客观合法性(“合理”),是因为它具有以下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客观存在)和嵌入结构中的依据(合理依据),包括:(1)本人或他人的生命、财产受到非法侵害; (2)当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或者财产受到不法侵害时,国家(或者特定的公共机关)缺乏保护,即国家应当保护被侵害的人。生命、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 (三)不法侵害情况紧急,受到不法侵害无法避免的; (4)对受到不法侵害的个人进行辩护是保护自己或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唯一手段。上述条件结构中嵌入了“正当防卫”所规定的法律原则,或者说,“正当防卫”的法律原则共存于这些条件组合而成的内部结构中。这种结构中蕴含的“法律原则”(法律规范的因果基础)是客观存在的,不依赖于我们的头脑,也不依赖于我们的知识和理解。
但如上所示,“法理”显然不是“物理”。正如规范不等于(自然)法一样,“法律原则”所蕴含的客观条件和结构也不等同于自然原则所蕴含的客观条件和结构。它们不能直接相互还原、相互解释。归根结底,法律法规或法律规范规定的(处理的)事项是人的生命或人的行为的事项。其中的“道”不是指“自然事物的必然规律”或“自然之道”,而是指人的生命。或人的行为及其处理方式的问题,即“人事之道”(简称“物之道”),广义上包括“为人之道”、“为人之道”、与人相处的方式”、“事物存在的方式”、“处事之道”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规范之道”(即实践理性的普遍规律)。康德)。自然之道是因果必然(必然),人事之道是实践中逻辑必然(行为规范)(即如果一定条件或客观事实因素存在,人们必然会根据逻辑做出某种行为) ,或者:已经做过的某种行为,必须在逻辑上被认为是合理的,比如“杀人换命”、“还债换钱”,这些“事情”在所有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必须被要求发生。这样做。推断出合理行为背后的理性基础的行为或逻辑称为“理性”)。相应地,“师道”所形成的事实条件结构中也蕴藏着因果规定(广义的“师道”之“因”,简称“事理”) )。
为了在阐述层面上简化复杂性,这里我们重点考察“法理”与“事务”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还可以进一步观察: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原则必须“源于事物的本质和客观现实”。换句话说,法律原则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们要么嵌入在法律规定的结构中,要么嵌入在法律规定(法律原则、成文法原则)中规定的条件(主要是行为要件和法律后果)中,或者嵌入在个案处理的事项中。 ,或者更准确地说,嵌入由行为事实的各种因素组成的结构中,作为对事件的判断(及其处理)的基础(个案中的“法理”)。然而,这里,行为事实本身的因素结构(顺便说一句:事实并不等于所要处理的事情/事物,但事实的因素结构构成了对所要处理的事情/事物的判断基础)处理,例如,谋杀是一个事实,杀人犯是否应该判处死刑是一个问题或待处理的问题),这可能嵌入法律原则(法律规范/法律规定的原则),并且首先所有的一切,都可能蕴藏着事物的原则(theprinciplesofhandlingthings)。所谓“理由”之事,此事无从谈起。比如,一个人故意杀人这一具体事实,实际上包含着很多需要考察和解释的因素。这些需要考察和解释的事实因素构成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本身就包含(或嵌入)了以下“东西”(例如,“以杀换生”的原则(理由):杀戮的行为)不正确,因为它违反正义、违反人伦、破坏和平(“正义”、“人伦”、“和平”等都是处理“杀戮”事务的合理规定)。这个原则(因果基础) “杀人求生”)还可以进一步分类或抽象,即对类似案件中的“原因”进行综合归纳为法律原则。例如,对类似杀人案件中“杀人求生”的因果规定进行了归纳作为法律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合理依据死刑的规定(刑法的基本原理)。
就事实原则与法律原则的关系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客观的“法律原则”或法律规范的因果规定具有“事实相关性”或“实际相关性”(Seinsbezogenheit)。 “法理学”从一开始就嵌入在法律规范所规定的类型化事项中。但如果深入考察就会发现,这些法律规范规定的类型化事项,都与个案处理的问题有关。案件最终与个案事实相关,作为案件判断的依据。即一切事项(法律法规规定的类型事项和个案处理事项)均以事实为依据。这说明法律原则在根本上是与事实相关的。脱离事实、脱离“事物的本质”、脱离客观现实,“法理”就无法解释清楚、无法理解。事物和事实决定了法律原则的本体论性质,不存在脱离事实关联性(本体论意义上)的纯粹概念性(虚构的)“法律原则”。
当然,在理论上,我们也不能把法理和事理完全划等号。在通常情况下,“事理”(狭义的)一词是指具体事项处理之理(每个具体的事情都有属于该事的处理之理或事情处理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其惯常的表达是:“这一个事情处理之理”或“那一个事情处理之理”,即,“一事一理”。法理则不同,虽然法理也必须从事实出发,特别是,个案中的法理的确断必须基于个案事实诸因子结构的考察和解释,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单独把“法理”视为基于某个特定事实之事情(“这一个事”或“那一个事”)处理之理,不是说每个事实都完全(或完整)内嵌一条只适用于处理某个特定事项的法理,即,不存在“一事一法理”(如上所述,法理乃是一个概括性用语,泛指法律规范/法律规整之理,其系抽象“事理”或同类“事理”的概括,适用于说明同类的多个有待处理的事项的根据),大多的情形是:个案事实中可能仅仅内嵌着有待处理的事项之法理(原因性的规定根据)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构成元素,也可能内嵌着一些尚未概括为法理的纯粹事理。本体论意义上的个案纯粹事理与法理之间本质上应具有一致性:真正的客观事理也就是事情/事项之法理的子类。
像“自然之理”(自然的必然呈现方式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可以被认识、发现、言说一样,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的)“法理”也可以被认识、发现、或者言说。在认识论意义上,“法理”同样可以表现为人的“言理”。此时的“言理”是人们对客观的“法理”之言说,这其中包括普通人对“法理”的言说和法学家(广义上包括从事实务的法律家)对“法理”的言说:前者可以视为有关“法理”的“常人之言理”(“常人之言理”并非等同于“常理”,“常理”乃指人类共通之理,其不区分普通人和专家,乃一切理性人共同持有的有关客观“法理”之言理),后者可以称为有关客观“法理”的学理(学术之言理或学说之理)。然而,有关客观“法理”的学理也并非都属于“真理”(我们可以把反映本体论意义的“法理”结构的认识再细分为有关“法理”的“意识”[感觉]、“意见”、“解释”、“信念”、“学说”、“知识”、“教义”、“原理”、“真理”,等等),只有那些真正反映客观“法理”结构的学理,才可以视为有关“法理”的“真理”(有关这一点,下文尚有专门论述)。所谓反映客观“法理”结构的学理,绝对不是“既在主观上、也在客观上不充分的视其为真(Das Fürwahrhalten)”的法理“意见”(Meinen),也不单单是指“只是在主观上充分,同时却被看做在客观上是不充分的”的法理“信念”(Glauben), 而是指“既在主观上、也在客观上都充分的视其为真”的法理“知识”、“教义”、“原理”。认识论上有关“法理”的“知识”、“教义”、“原理”本质上与本体论上客观“法理”结构具有同构性(同型性),达到学理与客观“法理”的完全相契合,以至于人们有时候把认识论上有关“法理”的学理与本体论上客观“法理”完全等同起来(或者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摹写”或“复写”),并把认识论意义上的“法理”用作分析、论证和评价的“理据”(或“理由”),进而作为立法、司法、守法的基础,构成法律文件、司法判决书、合同书、遗嘱、公证文书等等文件制作的学理支持理由(根据)。
不过,严格地说来,有关“法理”的“真理”并不是一个很贴切的表达,原因在于:如上所述,狭义的“真理”只适合于用来描述承诺自然世界事物“道”/“理”的“真实性言理”或“真实性道理”。这种真理的合适称谓是“事实性真理”(factual truth):就像我们在数学中所看到的“公理”,比如:“如果两条直线都和第三条直线平行,这两条直线也互相平行”;或物理学中的“公设”,比如:“不可能把热量从低温物体传向高温物体而不引起其它变化”,等等。由此看出,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首先证明的是客观事物之道的“真”(truth),更确切地说,真理实乃有关自然的必然呈现方式(自然规律)之“真”的“理”,其通常用陈述(描述)句来表达。而“法理”(比如,人有正当防卫的权利之理)的“言理”既要证明“法理”的“真”(在事实诸因子结构中内嵌的客观“法理”),而最根本的是要证成“法理”之“(实践)正确”(英语:[practical] correctness, rightness/德语:Richtigkeit),这个被证成的“(实践)正确之理”的实质是“正义”(法的先验终极规范性原理),故此“法理”也可以称为“正义之理”(the reason of the justice),其通常用规范语句或评价语句来表达。
综上,依笔者之见,在认识论上实际上存在两类性质有分别的“道理”:一类是以陈述句(描述性命题)、单称谓词语句和理论语句表达的“真理”(严格意义的,比如“事实性真理”/“经验性真理”[empirical truth,与经验相关的信息正确性]);另一类是有关本体论意义上的、以规范语句或评价语句表达的规范之理的正确言理(规范性真理/normative truth),笔者更愿意将后者称为“正理”(实践正确性之理或正义之理)或“义理”(道义之理)。正如我们在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哲学中所看到的,哲学家历来把前者称为“第一性真理”,而把后者称为“第二性真理”。如果一定非要把“正理”或“义理”理解为“真理”(广义的,或者泛称的,其实用“道理”一词表达更好),那么它只应在“似真的”或“适真的”(being truth-apt)意义上使用,即,所谓“正理”/“义理”乃是一定的人类共同体“视其为真(Das Fürwahrhalten)”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