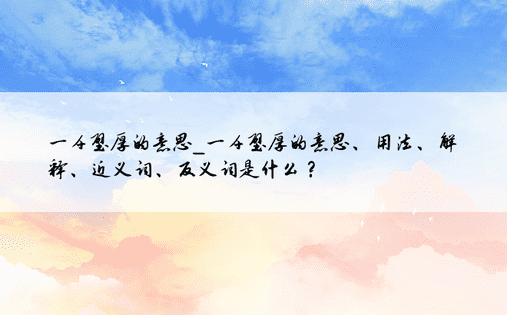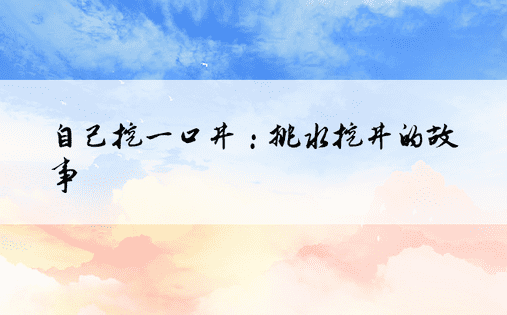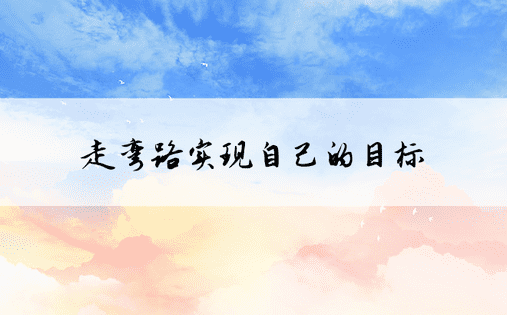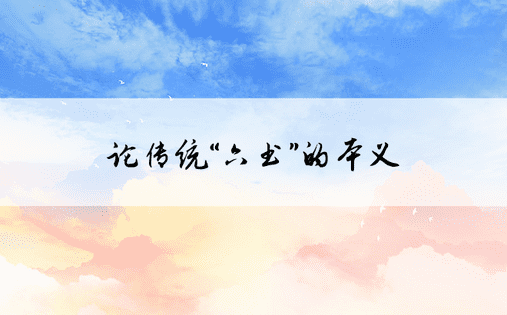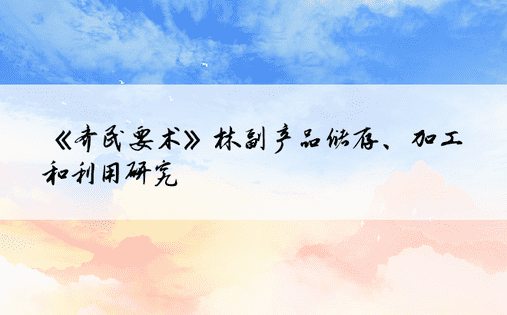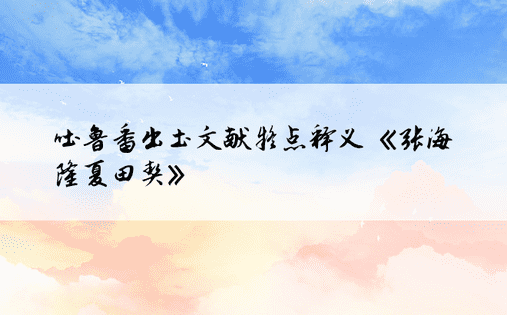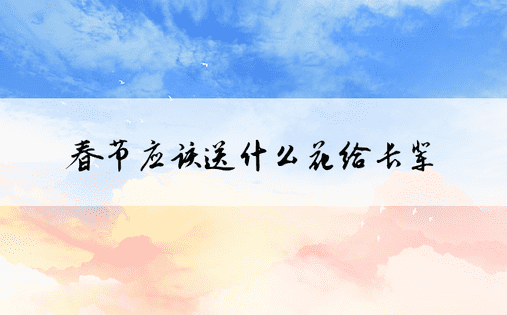论传统“六书”的本义
2023-10-05 18:54
1.汉字的本质
汉字是最古老、最有个性的文字符号之一。对其性质至今仍存在不同看法。阐明汉字的本质和揭示“六书”的真义可以说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科学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指出:“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系统:1、表意文字系统……这个符号与整个词相关,因此也间接与其所表达的概念相关。关系。该系统的典型例子是汉字。 2.通常所说的语音系统的目的是模仿单词中的一系列发音。”(《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结论不仅侧重于记录语言的本质特征和字符配置的基本依据
就记录文字的功能而言,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并无根本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连接文字的纽带是否为文字在意义和发音的相互促进中,汉字始终顽固地坚持其固有的意义特征,并不断采用新的方法来增强其意义功能,这体现在三个方面:1、当词语表达事物时汉字记载的意思是变化,汉字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调整其文字,例如“寺”最初来自“有”(主人的意思),后来由“存”(法律的意思)演变而来; “炮”本源于“石”,后由“火”等变化而来。 2、汉字中的借字向注音字的转变,已成为汉字演变的一个规律。例如,“PI”改为“避”、“幽”、“嬖”,“寅”改为“寅”,“舍”用于“舍”旁加“手”,“舍”改为“舍”。 “许”用于在“等待”旁边加“站”等。 3、从早期形声字的起源来看,它们不仅不是表音字的产物,而且显然是汉字顽强地维护其表意体系的结果。例如“考”加“老”组成,“朱”加“秀”组成,等等。甚至形声字中的一些注音符号也具有区分词语的功能。如“逃”与“袁”、“鹄”与“隼”、“无”、“沙漠”与“灓”等。可见,汉字,包括形声字,都是以意义和符号为基础的。 。
2、《说文》与《六书》
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处于文字学时代,其最初的目的是“正字”,即正确认识和书写汉字。 《说文叙》就是要明确阅读和写作两大问题。但由于许慎的博学多才,以及他对汉字形体的深思熟虑和全面考察,其成就客观上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引起了后世学者的浓厚兴趣,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和探讨。学习。 ,将其视为一部语言学专着。传统的文字学被称为“小学”,这最初表明它的出发点是很低水平的识字教学。正是由于两汉时期中国近现代经典之争中古代经学家的推崇,“小学”才成为考据和阐释儒家经典的基础,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解释古代文献,因而具有崇高的地位。
其次,对于《六书》,班固引用刘歆为“造字之本”。所谓“造字”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整体体系而言,即化词为词;二是就汉字整体系统而言,即化词为词;第二,就汉字的形体而言,即一个字形如何体现所记录的文字。许慎的“着书”应指的是后者,又说“得其意而言之”。因此,当时的《六书》就是解释“竹帛上书”的规定,也就是在许慎心目中“解释文字、解释经书”的“字规”。 。解读古文献的实用目的,也造就了《小学》所固有的形、音、义相互追求的传统方法。分析的对象是秦代规范的小篆,汉代学者所谓的“六书”就成为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形成规则的方法。后人对《
》及其《六书》的本性缺乏真正完整的认识,造成了各人说法不同的复杂局面。
班固所谓的“造字”和许慎所谓的“书写”,本质上都是将文字构造成文字形式,即“汉字配置”。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在古代,人类的认知思维必定具有注重形式和知觉的特点。在汉字的早期,先民的形态思维必须只关注字的意义和内容,即用字形来直接显示字的意义,以达到“目控”的目的。但这种“造字”的形成方法显然有其局限性,所以古人的形成思维的重点必然转向单词的读音。汉语是单一发音的根语言(孤立的语言)。音节数量有限,必然导致同音词增多,从而造成词义混乱。为了摆脱这个困扰,先民的结构思维自然发生了逆转,从注重单词的发音转向注重单词的意义。这一曲折的构想过程给先人带来了新的启示。最终,在汉字的配置上,同时考虑了字义和语音两个方面。根据这个构象思维过程的合理推测,“六书”作为构象方式的出现顺序大致为:象形——象义(指事物、理解)——装模作样——转注——形声。
需要指出的是,徐慎在《说文》中对汉字字形的排列表现出了明显的系统性思维。但他从未深入分析过“六书”(作为一种阵法)产生的顺序。想来,编排自然不会以汉字演变的史实为中心。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和历时两个层面重新思考和解释,以揭示传统“六书”的真正含义。
3。进一步分析传统《六书》
徐慎鱼《后叙》说:“仓颉初着书时,封面以象形为文,故名文;后来形声相辅,这就是所谓的“子”。又曰:“文学是物象的基础,文字是文字的基础。这是徐氏对9000多个小篆的基本分类,分为“文”和“子”两类:“象形、指物、理解”是“根据象”的反义词。后两者含象形)对“素”的“文”的解释;“佯、转注、音”是对“增肥乳”的“字”的解释。因为前三者是“以物为本”。 ”,而后三者则是从“文”的根源上诞生的。这意味着许慎所谓的“六书”并不是对汉字结构的完整分类。他所处的时代就文字学而言,甚至他对汉字结构的解释也不可能没有局限性,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为解释的“六书”的分类比较粗略;第二,“六书”的定义。 《六书》本身过于简单,又受到当时并行文体的负面影响;第三,每本书的例子太少,没有详细的分析。正是这些,给后续的争论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因此,有必要重新分析《六书》,重现其本义。
1。象形:徐世云说:“物是依体而画,如日月。”象形图取自物体的形状。过去有学者将象形文字分为单体和组合体两大类。 。事实上,按照配置方法,单体象形图是为了描绘物体,即用简单的笔画来描述词所指的物体,形成独立的图像。例如“子、自、支、北、它、净、网、行”等。组合象形是为了突出物体,即用相关物体的陪衬来显示所要表达的物体。例如“页、眉、果、聿、狱、须、血、州”等,其中“人、目、木、酉、牛、页、盘、河”均用于设定
2.指物:在徐的解释中,“观意”二字是关键。 《说文》文中所举的字例,其构成方式应分为两类:一类是象征意义,如“一、三、上、下、□、○”等;另一类是象征意义,如“一、三、上、下、□、○”等;指在物体上加有标记的方法,如“边、本、末、易、朱”等。前者多取自古代原始记录事件方式中的事迹。后者仅具有指示地点的功能,这是“六书”中争议最小的,无需多说。
3.理解:徐说的“比比交友”更准确的。 “会”有两个意思:“比较”和“了解”。所谓“比较”自然是指两个或多个部分的比较。这些部分可以是图像(不能独立转化为文字)。 ),或者它可以是一个字形。因此,“知”也包括两类:一是比较图形,二是结合字形。前者是根据事物之间的关系,将两个或多个图形放在一起进行直观比较。表达某个词的意义,其内容大多是对某件事过程的表征。例如“丞(后来的“郑”)、郑(后来的“郑”)、伟(Wei)、葛(@①)、“立、已经(知道怎么吃)、马上(知道怎么吃)、莫(黄昏)”等。后者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词组合在一起,依靠组成词的词义关系使人们理解新的含义。例如“丛、目、秋、占、明、洪、炎、苗”等。
4。假装:许世云道:“无实言,遂凭声托事,主帅如此说。”以今天严谨的思维来看,徐氏的定义似乎是指因读音相同而借词,但徐氏所举的例子却是指因引申而借词,引起了后来的各种争议。其实他误会了许慎。徐先生的初衷是让定义和例词统一起来,相互再造。也就是说,“借词”有两种:一种是谐音借词,即借词的本义与借词意义无关,而只是发音相同或相近;另一种是谐音借词,即借词的本义与借词意义无关,而只是发音相同或接近。另一种是释义借词,其中借词是一个词的本义与其借用意义相关,通常称为引申关系。前者如“难”,其本义是鸟名,借用“难”,表示困难和容易; “末”,本义是朝夕之“暮”,借用“末”,表示空话;后者如“令”,本义为命令,借用(今“引申”)县令的“命令”;如“令”,本义为“命令”。 “褊”,本义“一笑”,借用(引申)为狭义之名;徐以“令、常”为例谈借。显然,他也把“公子”这一具有引申但无差别含义的词视为“借用”。这在语言学时代是完全合理的。
5。注:许诗云说:“当我们构建相似的诗时,我们同意彼此接受,并且总是一样的。”后世对“传”的解释不下数十种。其中,“主义派”的代表流派有三个:姜生主张“音转注”说,戴震主张“转注互训”,朱俊升主张“转注为训”。延长”。要想查明许慎的初衷,只能采用“言出必行”的原则。 《说文叙》曰:“建之第一,立一为端;……齿成群,物分群……依形而延……端”结束。”他还解释说,“知义”云:“比较类比,以达成理解,从而看出命令。”据此,“建筑类比”的所谓“类别”应是“ “相似聚”和“类比交友”的类别,即“物”“类”,即词义上事物的类别。“以一”的“受”是《叙》所说的“见受”的“受”,就是大致标明事物类别的部首字,所以“立类”就是确立事物的类别,统一部首的含义。所谓“同意”,是指与部首符号所代表的同一范畴,“香雪”是“受之”的意思。这样说,“转注”的“转”就是意义转移,即意义通过引申字义或借用同音来改变字的字义;“注”是注解,即注入部首的意义,以明确原字形的意义。孙以让在其《名原转注揭橥》中说:“如果名字的名称没有特定的字,那么就根据其音义,在文字旁边进行训诂,以使其明确。”这就是徐的目的。因此,简而言之,译者改变了词义,注入了相关含义。
转义应包括两种:一是附加意义符号,如“花、酒、蛇、嫁、烧、暮”等,其中“老、行、虫、女、火、里”是最后添加的第二个是修饰能指,如“曰(说)、讣(go)、坚、措(cuo)、救济(zhen)”等,其中“辛、言、日、手”替换原词“言、行、月、金、手”,以适应意义的变化。有一点很容易引起学者们的误解,需要加以说明:《六书》中各书所例举的字,除“专诸”外,都是同一行的两个字;和“考、老”不是并列关系,“老”是类的第一个字(建类的第一个字),“考”是篆书字(同意互相接受)。许慎说,“考从老省”就是证据。
6。音声:徐曰:“以物为名,以例相辅,如江河”。过去学者普遍将“以物为名”视为“形”,将“举例相辅相成”视为“音”。这或许不符合徐的初衷。 《说文》 说:“名字是自命名的。”而《叙》中的“名字”二字是唯一看到的。当谈论写作时,它可能被称为一个字符、一篇文本或一本书,但不会使用“名称”。据此,所谓“以物为名”中的“名”应指人名、名字或词的读音。这也符合“托事之声”的说法。后一句“举例相得益彰”自然指的是符号。因为“比喻”就是比喻,使人明白。这也与“类比”相一致。 20年代的语言学家顾适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见他的《中国文字学》)。
相关推荐
-
品[yì qián bǐ hòu]解释 意思是先构思成熟,再开始写作,这样意境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