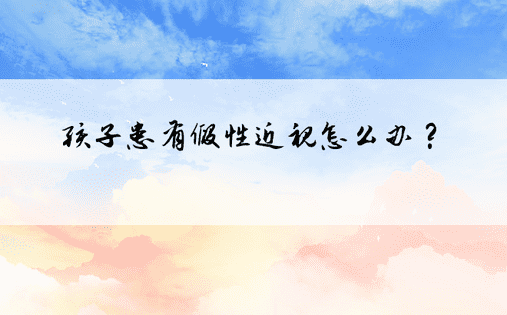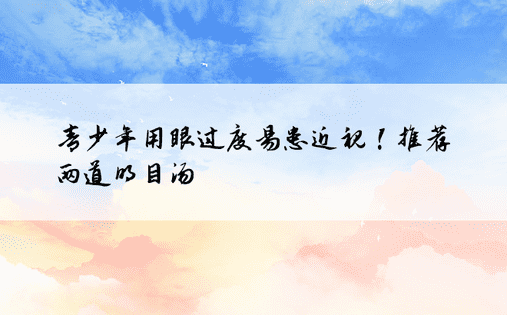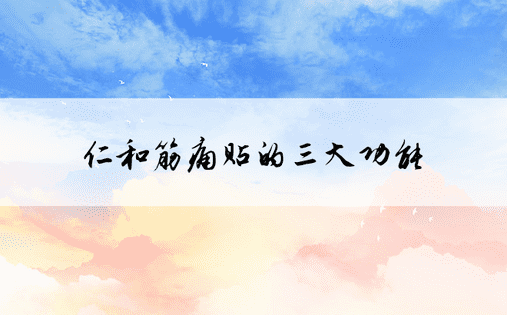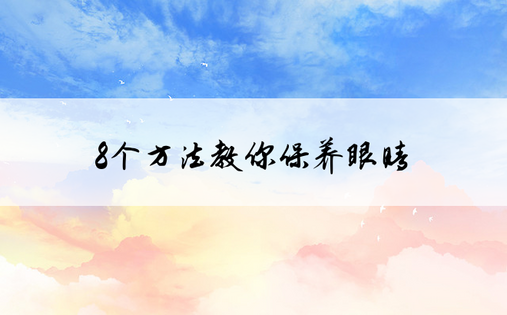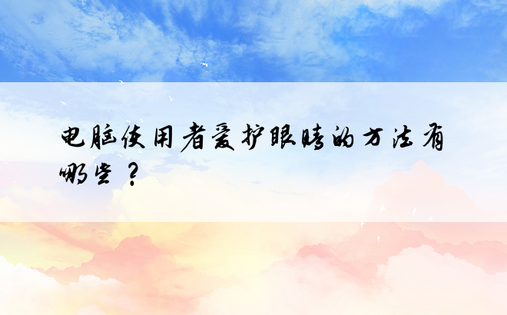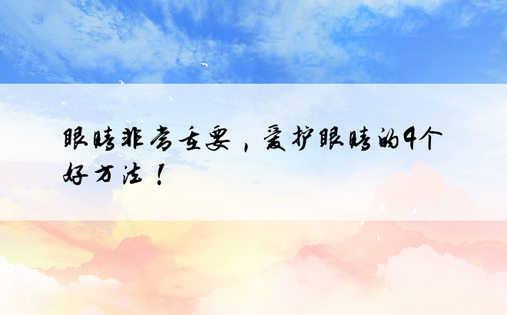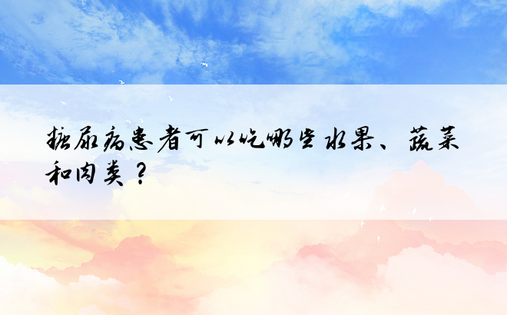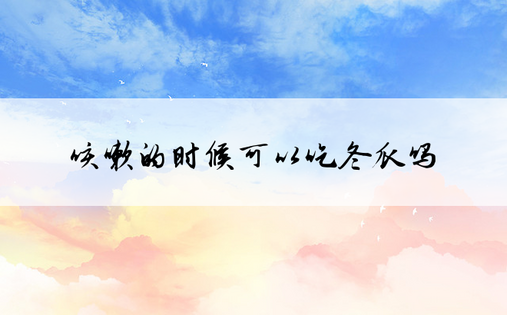【东篱】父亲的建军节(散文)
2023-09-30 23:12

父亲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入伍的铁道兵。每逢建军节,他都要哼起那首《铁道兵志在四方》的歌。他的声音就像车轮碾压铁轨,铿锵有力。“建军节”这天,我都要在父亲身边,跟着他哼那首歌。
我参加工作后,身在外地,不方便回家,建军节这天,一定要在电话里问父亲“建军节”好。有时候,情不自禁和父亲一起在电话里唱那首歌,唱响父亲的青春岁月。
和平时期的铁道兵是极少扛枪的士兵,他们大多时候衣衫褴褛,尘垢满面,被当地百姓戏称为“叫花子兵”。他们虽然没有上阵杀敌,巡边戍防,但他们无怨无悔,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延伸了铁路,所修建铁路占同期全国新增铁路总里程的三分之一,加强了新中国边疆与内地的联系,以血肉之躯重塑了中国的地理格局。他们为现在被称为“基建狂魔”的中国名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每当看到公路上车流滚滚,铁路线上的高铁风驰电掣,我马上想起父亲,想起那些铁道兵。
时代的列车飞速向前,我觉得还在载着他们的精神奔驰。
父亲始终珍藏着他的退伍证。1976年唐山大地震,房倒屋塌,见家里人无恙,别人都在抓紧清理粮食、衣物之际,父亲却小心翼翼地去废墟里寻找他那张珍贵的退伍证,抖落尘埃,怀揣温暖。再用红色绸缎布包好,置于母亲的存钱木盒里。
别人家的孩子不敢翻动父母的钱匣子,而我是例外。每每去看,父亲就默默守在旁边。他希望我去阅读他的光荣历史。
曾问父亲铁道兵的徽章放哪了,父亲不自觉地摸摸前额,又摸摸左胸,摊手说,那可不是谁都有的,自己争取吧。
那时候母亲经常跟我们讲,她结婚前和奶奶一起到部队看望父亲的故事。那些年中越边境战火纷飞,父亲所在部队,接到了准备开赴战场的动员命令,战士们开始纷纷写请战书、家书甚至还有遗书。很多家属火急火燎地赶往部队,其中就包括奶奶和母亲。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部队最终没有开赴战场,这,成了战士们终身的遗憾。长辛店、周口店、猿人洞都是母亲经常跟我们提及的地名,仿佛比家乡的村名还亲。叼烟袋的东北大姑娘、拿着辣椒当饭吃的四川姑娘、一句话也听不懂的广东姑娘,都是母亲津津乐道的对象。母亲的见识来自铁道兵的环境。那时候老叔只有两三岁,也跟着奶奶一起来到部队驻地,在营房里到处乱跑。一次母亲找不到他,就四处呼喊他的名字,就有战友好心地提醒“你儿子往那边跑了……”臊得母亲满脸通红,说:“那是老兄弟!”父母的爱情,写在铁道上。我常常这样跟朋友说,我为父母有如此浪漫的爱情经历而自豪。
父亲五音不全,我很少听到他唱歌。但父亲有了高兴的事总喜欢哼唱几声,且总是那个调调。那是铁道兵之歌《铁道兵志在四方》:“背上了那个行装,扛起那个枪,……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我高考那年报志愿,征求父母的意见。憨厚的父亲竟脱口而出,你就写“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时觉得父亲一时兴起说说,但后来我长大后琢磨这句话,这是一个铁道老兵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决定的。有些事,有些话,有些思想一旦深入骨髓,就成了身体的一部分,跟随一辈子。一朝当兵,终身是兵。父亲一直以曾是一员老兵为荣,以身作则,也把我和妹妹当成一员小兵教育我们成长。
这些年在外闯荡,遇到多少事,我心中始终有两根向前的铁轨。铁轨就是我的精神基因,来自父亲的传承。
二
我终究还是没能当兵,走了去上大学、包分配工作的路子。我在北京工作以后,曾多次带父母过来观光旅游。有他们曾经到过的故宫、动物园等,也有从没到过的颐和园、长城、天坛、圆明园等。几十年的岁月,北京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游人如织,这些都让久不出门的父母眼花缭乱,赞叹不已。
可粗心的我,从没想过带他们走一走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军营,看看火车穿过他们曾经凿穿的大山隧道。父母是沉默的,就像来北京游玩,每次都是我三番五次劝说着才出来。父母从没有提出要去周口店,我也总自以为是地认为带他们看名胜古迹,吃南北美味,把最好的给他们,他们就满足了。殊不知,由于我的粗心,险些酿成他们终身遗憾!
那是2006年,随着电话的普及,很多失散的同学、战友、同事等又开始逐渐建立起了联系,年轻人更是建起了各种QQ群。父亲的一位远在丰润的苟姓老战友的生意风生水起,有着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他委托当地战友联系散落于全国各地当时一个连队的战友,定于那年八一建军节聚会。父亲初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像个孩子,脸上每个皱纹都绽开了,他说三十多年了,我们这群“黑老铁”(铁道兵相互趣称)还能再见面,我不是在做梦吧。说起这位苟叔叔,父亲说年轻时候在部队就属他调皮,有主意,当时都叫他“小狗(苟)子”,现在可是变成苟总了,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认出我这“拱土坷垃”的老战友!
父亲提前把花白的头发理成寸头,仔仔细细刮了胡子,“八一”那天穿上母亲特意给父亲买的一身带风纪扣的军绿中山装,和同村的几位战友一起登上了苟叔叔安排好的前来迎接的大巴,赶往丰润某宾馆赴约。
回来后几天里,好像父亲的酒一直没有醒,脸总是红扑扑的,抑制不住兴奋,他跟我和母亲喋喋不休地描述着聚会的场景。那是怎样的场景。一群久经风霜六七十岁的老人,曾经的首长,曾经的战友,亲切的话语,激情的拥抱,一声声感叹,一句句祝福,眼角都泛起激动的泪花。苟叔叔逐一和大家握手,拥抱,打招呼。他竟能叫出父亲的名字,说这不是猪倌田金明吗?父亲在部队干过一段时间饲养员,他像对待战士一样对待猪崽儿,每天赶着猪出操,跑步,就差喊口号了。猪被父亲调教得身体健康,产子率高,仔猪成活率也高,肥肥壮壮。为此父亲还受到连队的二级嘉奖,他的事迹被战友编成快板儿书在部队里表演,所以被戏称为“猪倌”。父亲后来复员转业到村里能当上兽医,也与他当时的养猪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父亲经常说,他是“铁道学院”毕业的,也是科班出身。不以位卑而牢骚,这是父亲给我的言传身教。
战友们聚会的高潮还是大家合唱《铁道兵志在四方》,歌声嘹亮,大家的眼睛都闪着泪花。临别,苟叔叔做最后的总结,最后有几句话父亲记得很清楚:“……有人说铁道兵番号没有了,铁道兵就没有了娘家,我‘小苟子’在这里放句话,有我‘小苟子’在,这里就是咱们连部,永远都是大家的娘家……”台下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抽泣声。
娘家?那么艰辛的岁月,那么艰苦的环境,以“娘家”相称,这是他们的温暖情怀。凡是成长的地方都是“娘家”,这样的情感意识,也一直珍藏在我心中。
父亲那个愿望更强烈了,就是想到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再去走走,看看。但是他这个心愿只对母亲说了,母亲也没对我说。他们总是怕麻烦别人,这个别人也包括我,他们唯一的儿子。粗心的我却是一直没有察觉到。
再好的风景,都不如父亲的青春岁月美。我理解了父亲对风景观,就像一个人爱家,家就是无与伦比的风景。
三
父亲年近七旬,但身体尚好,只是有点耳背了。他每天还坚持在物业打扫卫生,下地干活儿,劝也劝不住。
也好,他喜欢和别人说起年轻时当兵的事。一次,本村的一位战友找父亲闲聊,我正好在家。他们聊到曾经的军旅生涯,聊到北京西南的大山,周口店,隧道,聊到当年牺牲和现在去世的战友,又是一阵唏嘘。突然,那位战友说,听说咱们的军营还在。父亲的眼睛明显放出了光:“还在?太好了!”接着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要是此生还能到周口店走一遭,这辈子就没啥可遗憾的了!”
父亲的心愿就被我记住了,在2012年八一建军节那天终于达成了父亲的心愿。
父母是先一天到北京和我会合。现在的交通就是方便,车上六环转大半圈,上京石高速从窦店出口出去没多远就拐进了大山。房山区属于太行山山麓的一部分,道路两侧是耸立的高山,周口店再往前就是素有北方小桂林之称的北京十渡旅游度假区。雨季,拒马河河水暴涨,几乎与道路齐平,湍急奔流。那天风轻云淡,虽是伏天,可清凉的河水消退着炎暑,车子不开空调,打开窗户,也觉得凉爽宜人。
到了周口店,我试着在导航搜索“营房”“火车站”的字眼,附近没有匹配的。我开玩笑问父亲,还认识去部队的路吗?父亲干笑一下,说,都变了,以前这里都是土路,全是秃山,哪里还认得出?我说具体哪个村还记得吧?父亲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高家坡”。
车子拐上了进山的小路,蜿蜒向前。母亲望着两侧高低起伏的峰峦,不住地感慨,说,原来她和奶奶就是坐车到周口店再走进大山的,路边这个破旧荒废的供销社,她还曾到里面讨过水喝;山阴处那块大青石头她们也曾歇过脚,父亲还给她采过一束野花。这些细节,是父母的爱情样子,母亲不说透,我也懂得。
车子拐下主路,进入一个残破的村庄,导航显示终点已到。车停下,前面恰好就有一条横亘的铁轨穿过。父亲下了车,眼神迷离,似乎在脑海里对接曾经的记忆。生活了四年,阔别了四十年,父亲的心里一定波澜壮阔。我搀着母亲,默默地跟在父亲身后,徐徐前行!父亲先用石子在钢轨上轻轻地敲击,铁轨“哒哒”地回应,像两位阔别已久的亲人在诉说什么。后来石子敲击的声音渐渐变得激昂起来,好熟悉的旋律,仔细听,好像冲锋号的节奏。远方的战友啊,你们可曾听见一个老兵的呼唤?父亲粗糙的手又在铁轨上摩挲了好一阵,就像当年我小时候他亲切地摩挲着我的头。穿过铁路路口,不远处是一个山塘,父亲说,这原来是一座山,筑路基需要石子,他们部队就把这座山给扳倒了,敲碎了垫在铁轨下。很多战士脚趾甲都曾被砸掉,也包括父亲,我见过他的两只脚上都有粗糙变形的趾甲。
一辆货运火车恰好驶过刚才的铁轨,拉着汽笛“哐啷哐啷”地呼啸着钻进了不远处的山洞隧道。父亲一动不动地目送火车远去,他说汽笛是向他们牺牲的铁道兵致敬的,山脚下曾经埋着他的战友,那是为排除哑弹不幸牺牲的老乡。说着父亲竟然从包里翻出几沓纸钱,在地上画了个圈圈,放了进去,他先点燃一根烟,再点燃烧纸,嘴里默默叨念。火光摇曳,一阵山风掠过,在火堆前形成一个小旋风,把纸灰卷起飘向大山。父亲说战友一定是收到了,他在地上沉默着坐了很久,抽了大半包烟。
父亲一代人有着自己的怀念方式,我呢?此时有了记下铁道兵情怀的想法。让父亲不至于离开这里失落,唯有文学可以安顿父亲的灵魂。他喜欢看那些关于当兵人的文章,一张报纸也把看半天。
我说,中国现在开山打隧道都用盾构机了,是中国自己研制的,又快又安全,这盛世已如他所愿。父亲听后,露出微笑。
我们折回村子,父亲凭着记忆往营房的方向走去。这个村子和当下中国大多数山村一样,房屋空置破败的太多。那些老房的屋顶上不是常见的灰色瓦片,而是用石片叠压而成的屋顶。清晨,村子里人很少见,也鲜有鸡鸣狗叫,倒是各种杂树参差错落,亭亭如盖。我们一行到了村北,见树荫掩映下,有一个紧闭的荒芜大院。父亲说,这就是军营了。
我透过锈迹斑斑的铁门向里张望,但见一排排低矮的平房,窗户油漆脱落,玻璃已经残缺,房顶长满了青苔,墙上爬满了爬墙虎,地上也满是杂草,几只斑鸠站在窗台上发出“咕咕”的叫声。令我想起杜甫《十五从军征》里“兔从狗窦出,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的凄凉诗句。但离我最近的山墙上的红漆字我还能依稀可辨,是鲜亮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父亲经常把这八个字挂在口头,我摄下来,转给父亲的手机吧。
一位和父亲年龄相仿的村民打此路过,就笑问父亲是不是曾经是这里的战士。父亲惊讶道:“您怎么知道?”村民嘿嘿一笑,说:“近些年,每年都有曾经的战士来访,我们都见怪不怪了,走,到家里喝杯茶去!”见村民说得诚恳,父亲倒也乐得找个人聊聊,我们就随着主人进入他家。
他家院子倒是很大,两层半新的房相通着,院子里栽种着各种时令蔬菜,长势正旺。村民沏上茶,又摘来新鲜的西红柿、黄瓜,用压水井的井水洗了摆在盘里。他对我们说,十年前儿子结完婚就去城里买房了,就剩下他们老两口守着这个大院儿,村里人越来越少了,平时找个说话的人都少。他是跟着解放军的屁股长大的,也经常偷跑去军营,那年月家里吃不饱,解放军叔叔会偷偷给他大馒头。军营在1984年就归了地方,开始作为小学学校,后来招不到几个学生,学校就合并到别的村了。再后来又改成养殖场,养了羊。养羊的老头死后,就荒废了……村民很健谈,父亲大多数时候都是默默抽烟,不愿意放过村民说的任何一个细节。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年40万的铁道兵说散就散了,一个垂垂老矣的村庄看来也坚持不了太久了。时光总要放下一些东西,剩下的唯有感慨。父亲要靠回忆找回曾经,陈迹不旧,永远清晰。我的担心可能是多余了。
相关推荐
-
平时要密切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因为很多疾病正在悄然发展,你的身体就会拉响警报。能细心留意的人只有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