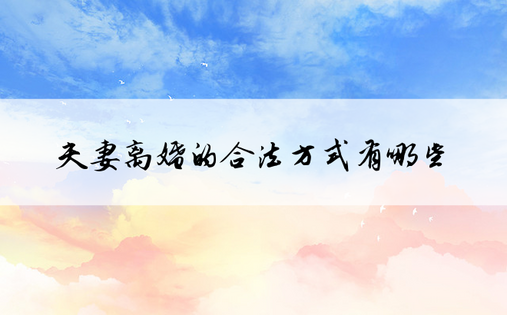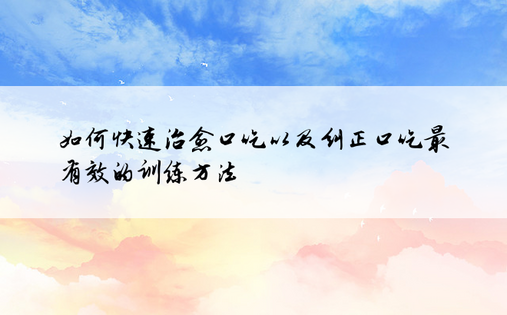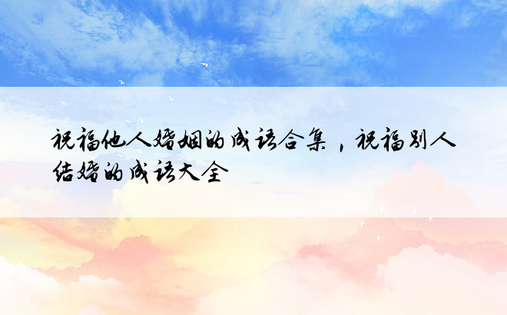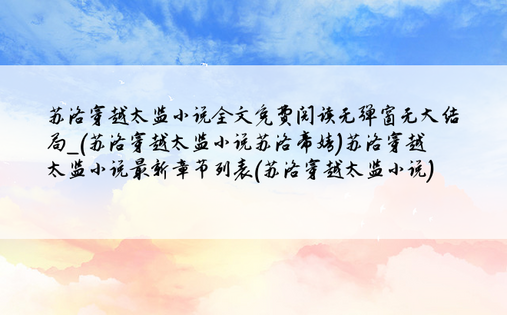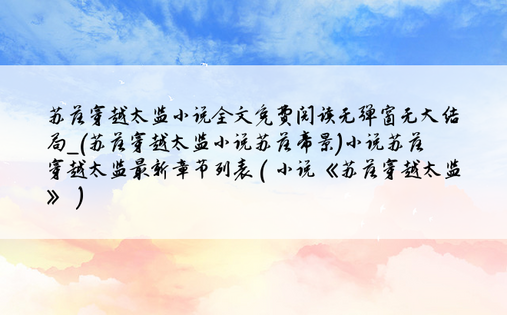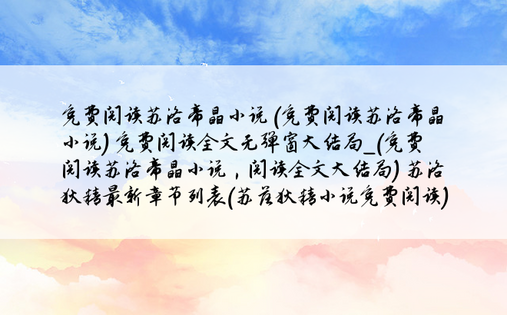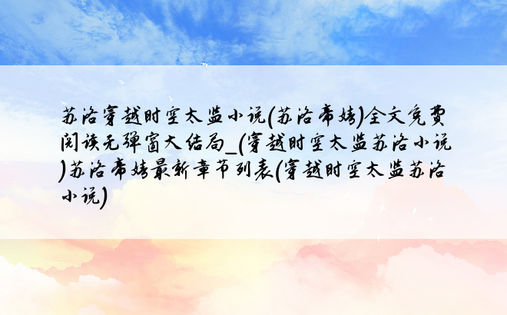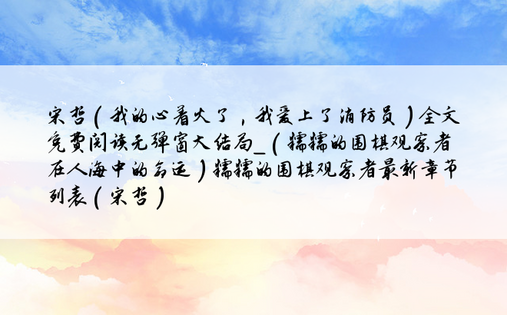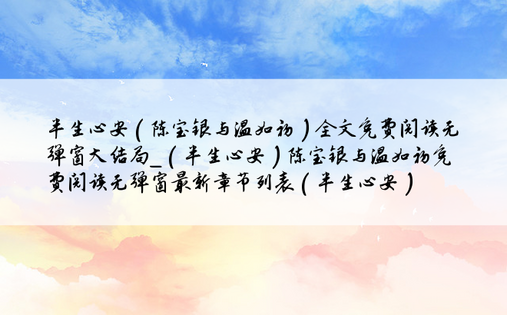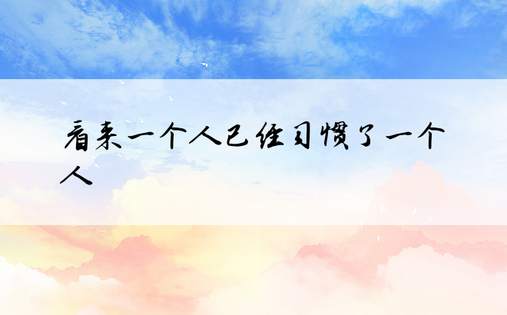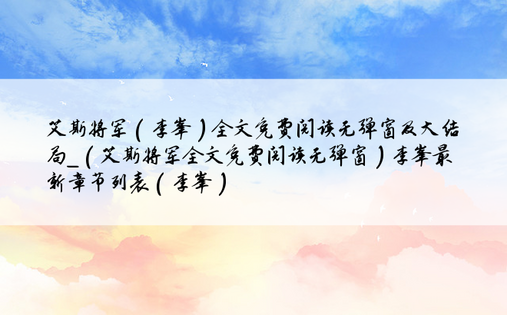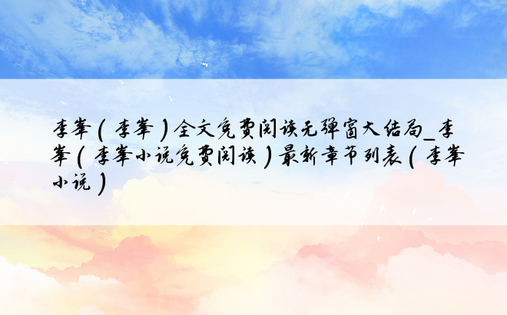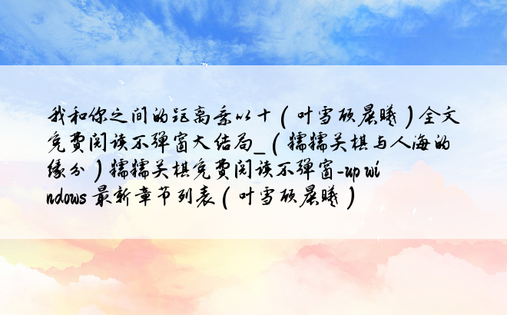爸爸的假期电影,我与父亲征文‖爸爸的自行车
2023-09-23 14:42

无论是养育型父亲、学习型父亲、传统型父亲还是现代型父亲,“父亲”永远是一个刚柔并济的词,没有这些属性,它会在平淡中给我们最永恒的安全感。
我忘不了很久以前看到的一幅美丽的画面:努力寻找虫子、草籽和露水喂饱饥饿的小鸟的“妈妈”,在阳光明媚的山坡上奋力搭建起这个温暖的小窝的“爸爸”。
我还记得早期教科书中朱自清的《背影》,描述了深沉的父爱,像月光一样平凡而美好,无声而温暖。
不同的人对父爱自然有不同的感受和体验。
值此父亲节之际,《大众日报》客户端和《大众日报》收获副刊推出了一篇以“我和我的父亲”为主题的短文,讲述你和你父亲的故事。风格不限,内容可以是对过去的回忆,你的假期想法,或者你在假期的亲身经历。
投稿邮箱:support@www.ainchannmyay.com
爸爸的自行车
王亚宁
一
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有一辆自行车。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一辆半新的永久牌28自行车,那是农村人家里最珍贵的财产。怕撞到,爸爸用塑料胶带把三角形的架子包起来,后面的架子包起来。因为没有同色的胶带,爸爸自行车的三脚架是红白相间的,架子是黄绿色的。这辆五颜六色的自行车成了我父亲的宝贝。爸爸开车送我去探亲赶庙会,让我的童年快乐而自豪。
当时,我的父亲是我们村小学的一名私人教师,月薪六块钱。这六块钱是我们一家十口一月的开销。元是给家里买盐和油,给奶奶和妈妈阿姨买针和针,给刚上学的姐姐买铅笔和橡皮,给年迈的曾祖母买药品,还有一点是过年时我们偶尔添置新衣的。那时候,六块钱似乎足够买下整个世界。也可能是当时我的世界太小,只能装下村里的小代理店。
其实,我不知道的是,我父亲骑着自行车四处奔波谋生。刚开始,父亲看中了一家在暑假卖尼龙网袋的小生意:当时流行用尼龙网袋包装东西。城里人去亲戚家,买了一斤零食和一串香蕉,用网兜装好,在邻居羡慕的眼光中,从街角走了。送东西的有面子,收东西的更有面子。爸爸骑上自行车,跑了四十英里去宝鸡。花6美分,一个人找到一个熟人批发100个网袋,在离家20多英里的一家工厂门口拿到。一毛钱卖一百可以赚四块钱,相当于爸爸半个多月的工资。第一次批发100个网袋花了爸爸5天时间才卖完。妈妈说,虽然七月的太阳把爸爸晒得像包公一样黑,他每天骑着自行车来回四五十英里,但爸爸很满意。第二次,又批发了一百个。每天,我们带着干粮和一瓶水,开开心心地骑着自行车做小生意。可惜的是,这百个网袋只有几个被第三次卖掉,我父亲被工商局的人盯上了,剩下的网袋全部被没收。原因是为了杜绝资本主义的萌芽,防止人们为了私利而投机倒把。爸爸的第一笔生意就这样结束了。

生活必须继续。秋天,爷爷种的旱烟叶子干枯了。星期天,父亲骑着自行车,背着一捆捆的烟叶,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给村里想抽烟却抽不起烟的老人卖烟。有时候,骑着车,翻山越岭,会一路走到千阳。当我到家时,往往是半夜。
1980年后,私营企业被允许。那个暑假,爸爸骑自行车早出晚归。他从村里有余粮的人那里买了小麦,送到城里的面粉厂,换成了面粉。他还把它带到工厂门口,卖给工厂的工人,并换了一些粮票和钱。爷爷很细心,一部分补贴家里,一部分寄给刚考上省城大学的叔叔。
这些过去的事情是我父母近几年断断续续告诉我的。当他们交谈时,他们笑着说着,好像在讲有趣的故事。我反复思考,慢慢体会到其中的艰辛。我明白,那时候,爷爷奶奶和父母竭尽全力只是为了生活。他们张开宽大的双臂,为我们挡住了人生的苦雨;他们默默的肩负起所有的艰辛,让我们的童年无忧无虑,充满幸福。
二
初中的时候,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两个叔叔和三个叔叔也完成了学业,加入了工作。家庭生产保障后,家里还有余粮,加上爷爷的精心算计,整天吃粗粮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另一个好消息是爸爸可以通过考试了,私立学校将改为公立学校。那个寒假,除了吃饭的时候骑自行车,其他时间爸爸都呆在学校复习功课。过年的时候,我们村唱了一出大戏,舞台离学校不远,爸爸就没出去看看。功夫不负父亲,他成了第一批从民办到公办的教师,工资一下子涨到了32元!爸爸再也不用这样到处跑了。
很快,我就要上高中了,那个时候我不会骑自行车。周日下午,爸爸早早地把车擦干净,把贴着妈妈烙的锅盔的布袋绑在车前。我坐在车后面的架子上,父亲蹬着车送我到离家二三十里的县城高中。周六下午放学后,爸爸早早就在学校门口等着,接我回家。来回的路上,我和爸爸聊了一会儿。我抓着爸爸的后裙,一路欣赏着野花,吹着微风,觉得自己抓住了所有的快乐。
我终于学会骑自行车了,爸爸。不
用再接送我了。一晃就到高三了,我们要补课了。每周只有一个下午的休息时间,让学生回家拿馍、拿生活费。我家离得太远,冬天的时候,天又黑得早,一往一返,时间太紧,爸妈也不放心我一个人来回跑。于是,爸爸就又骑上自行车,每周星期天来给我送东西。常常是星期天上午第二节课间的时候,我从教室出来,在阳台就能看见等在校门口的爸爸和他的自行车。我飞奔下去,爸爸解下绑在车头上的一大袋子香喷喷的锅盔馍,又把五元钱塞在我手里,叮咛几句“吃好,穿暖和”,就又匆匆回家了。
那一个星期天,早上下雪了,雪虽不厚,但落在地上,很快冻住了。第二节课间的时候,我站在阳台,望着校门口,一直到上课,都没有看见爸爸和他的自行车。“爸爸今天不会来了,路那么滑。”我一节课都没上好,既希望爸爸不来,又希望爸爸来。上周爸爸送的锅盔早已吃完了,钱还有一块多,够吃几顿的(我们那时的饭主要是汤面片,二两五分一碗)第三节下课,我还是忍不住跑出教室。校门口,爸爸正在翘首张望。我挥着手,喊着爸爸,冲了出去。爸爸笑呵呵地看着我说:“不小心滑了一下,车子链子断了,推着走了一大段,才碰到一个修车子的,就来晚了。”我这才注意到,爸爸的腿上蹭了很多泥,装馍的袋子却用一块塑料纸包着,干干净净的。爸爸和我说着话,取下了帽子擦汗,头上的热气一下子冒出来了,雪花落在头上,很快就消失了。上课铃响了,我跑回教学楼,在阳台上回头的瞬间,我看见爸爸高高扬起手中的帽子,在越来越紧的雪花中,向我挥舞着,泪水突然就涌出了我的眼眶。这一幕,三十多年来,一直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每当我对爸爸稍有顶撞时,想起爸爸头上的雪花和他的自行车,我就深深地自责不安。
三
在我们的大家庭里,爸爸一直都是一个守望者。先是二叔三叔相继走出家乡,去外地求学工作;后来是姐姐、我和弟弟,再后来是堂妹堂弟。一个一个的农家子弟,拼命地读书,终于走出了贫瘠的乡村,端上了铁饭碗,但根却一直留在故乡。我们候鸟一般,过年时会准时地飞回家。爸爸的自行车,就成了我们与家之间最后一段距离的渡船,而爸爸,就是那个摆渡人。二叔在遥远的西藏工作,每两年才能探一次亲,回来看望年迈的爷爷奶奶。春节将近时,爸爸就收到二叔发来的电报(那时候村里还没有电话),电报一般就几个字:几月几号归。到了那一天,一大早,爸爸就骑上自行车,到二十多里地外的虢镇火车站去接站了。到中午或下午,会看见爸爸自行车后面带着二叔,侧面斜挂着二叔的行李包,出现在奶奶看了一遍又一遍的村口。我小时候很少想事情的细节,长大后,我常常想: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手机的年代,爸爸怎么凭着一个大致的时间,接上叔叔?我想不通爸爸一大早到了虢镇火车站,怎么渡过那漫长的等待时光?问爸爸时,他说:“怎么会那么笨,一直站在哪里等?”原来每次到车站后,爸爸寄存好自行车,先去看列车时刻表。二叔从西藏经成都回来,他就看从成都来的车几点到站,看准时间后,就去街道转转,顺便赶个年集,买点年货,等时间差不多了,就候在车站。那时的绿皮火车很慢,还老晚点,到点了车没来是常有的事,那就不敢再离开了。爸爸就一直在站上等着,晚点多久谁也说不准;三叔是从西安回来,西安西行在虢镇停的火车很多,提前写来的信只说好是哪一天回来,三叔会买上哪一趟车的票,当时也不知道。爸爸接三叔时,就一直不敢远离,车站有不少象棋摊子,爸爸就蹲在棋摊旁,边看人家下棋边等。爸爸一看下象棋就入迷,有几回,三叔出了站,自己转悠着找到爸爸,哥俩才一起回了家。接我们姐妹时也几乎一样。
爸爸的自行车,载着一个一个疲惫的游子,回到家乡,充足了能量,又载着我们,把我们一个一个送到远方去求学、打拼。而爸爸,一直都是那个守望者:守着辛苦一辈子的爷爷奶奶,守着人口越来越少的家,守着我们村的小学,把村里一半左右的人,变成他的学生,变成撒向四面八方的蒲公英,把他的满头青丝守成了稀疏的白发。

四
爸爸那辆花花绿绿的自行车,比爸爸早一年退休了。车座换了几次,后面货架也换了几个,轮胎更是补了又补换了又换,终于再也换不了了。我们想给爸爸买个电动车,爸爸坚决不要。说他马上退休了,要车子没用了。村里也早通上了公交车,我们回家也不用去接站了。他就在家里下下棋、打打牌。
爸爸退休时,弟弟也已经在西安安家了。小侄子原来留在家里,妈妈带着。三岁时,该上幼儿园了,弟弟把爸妈和孩子一起接到了西安。爸爸就又给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买了一个儿童座椅绑在后面货架上,开始了接送孙子的退休生活。这自行车一骑,又是十年。
爸爸属牛,爸爸今年七十二岁了,依然精神矍铄,一起走路时我常常被落在后面。骑上自行车,在人少的街道,爸爸会蹬得飞快。我们在后面看着担心,不让他骑,他总说:“没事,骑了一辈子了,能控制住。”
春节前,爸妈回到了老家,我回去陪他们住了一晚。早上醒来,我赖在暖暖的被窝里,直到妈妈做好早饭,我才慢悠悠地起床。走出卧室,爸爸已给我端来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脸水,我把脸埋在毛巾里,泪流难止。这样的温暖,我不知道我还能拥有多久?
相关推荐
-
情感知识很多。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询问各方面的问题。今天欣东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如何快速治愈口吃。纠正...
-
有时候一句话就能让人对你刮目相看。这与好句子的积累密不可分。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祝别人结婚的成语(合集)...
-
帝景愕然的看着苏落。我心里不禁有些不可思议。一个困扰她和众多辅导员的问题,被苏落解决了。最重要的是…...
-
全后宫都在混乱。各个宫殿建筑中,纷纷传来命令。只有一个目的。找出新任首席内部官是谁!不同阵营的人开始...
-
我从消防队出来,我还穿着宋哲的短袖衬衫,写完笔记,宋哲提出带我回家。“从现在开始,吹风机用完后必须拔...
-
日复一日,十九岁那年,长公主回来了,听说我暂时留在首都,估计有一段时间不会回来了。公主带着他离开了。...
-
一晚上疲惫不堪,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顾晨曦确实很擅长这一点。尽管这是我的第一次,他还是把我榨干了。...